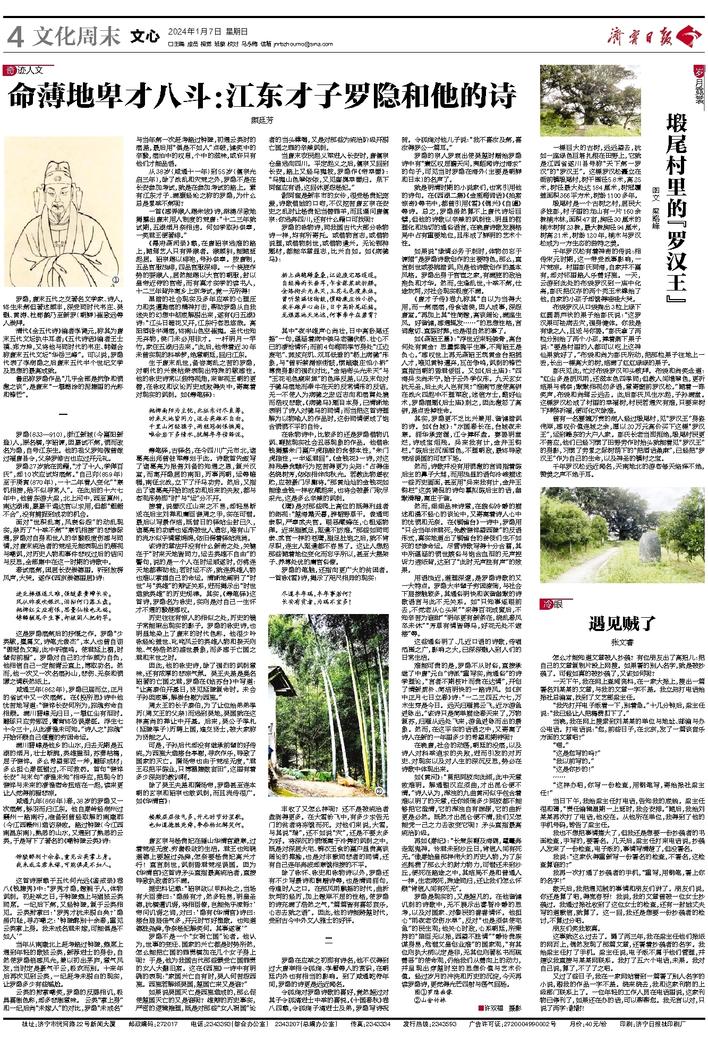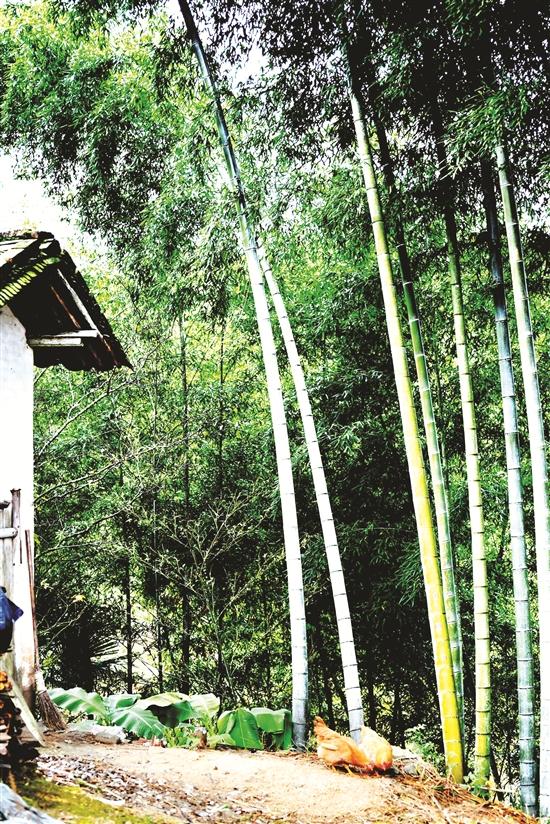罗隐,唐末五代之交著名文学家、诗人,终生未第但著述颇丰,深受同时代韦庄、吴融、黄涛、杜荀鹤乃至新罗(朝鲜)崔致远等人崇拜。
清代《全五代诗》编者李调元,称其为唐末五代文坛执牛耳者;《五代诗话》编者王士禛、郑方坤,又将他与同时代的韦庄、韩偓合称唐末五代文坛“华岳三峰”。可以说,罗隐代表了李商隐之后唐末五代半个世纪文学及思想的最高成就。
鲁迅称罗隐作品“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是唐末“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一
罗隐(833—910),浙江新城(今富阳新登)人,原名横,字昭谏,因屡试不第,愤而改名为隐,自号江东生。他的祖父罗知微曾做过福唐县令,父亲罗修古也应过开元礼。
罗隐27岁就在贡籍,“才了十人,学殚百氏”,却10次应试均落第。“自己卯(859年)至于庚寅(870年),一十二年看人变化”“寒饥相接,殆不似寻常人”。在此后的十六七年中,他曾东游大梁,北上河中,西至夏州,南达湖湘,屡屡干谒达官以求用,但都“龃龉不合”,没有捕捉到成功的机会。
面对“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动乱现实,亲历了“十举不第”“寒饥相接”的悲惨际遇,罗隐对自身和世人的辛酸极度伤感与同情,对唐末统治者的荒淫无能表现出的蔑视与嘲讽,对历史人物和事件悲叹过后的诘问与反思,全部集中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
春试落第,困居长安崇德里。听到放榜风声,大哭。遂作《西京崇德里居》诗:
进乏梯媒退又难,强随豪贵殢长安。
风从昨夜吹银汉,泪拟何门落玉盘。
抛掷红尘应有恨,思量仙桂也无端。
锦鳞赪尾平生事,却被闲人把钓竿。
这是罗隐落第后的抒慨之作。罗隐“少英敏,擅属文,诗笔尤俊杰”,本人也曾自诩“弱冠负文翰,此中听鹿鸣。使君延上榻,时辈仰前程”。罗隐对自己的才华颇为自负,他相信自己一定能青云直上,博取功名。然而,他一次又一次名落孙山,悲伤、无奈和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咸通三年(862年),罗隐已届而立,正月的省试中又一次落第。在《投所思》诗中他忧苦地写道:“憔悴长安何所为,旅魂穷命自相疑。满川碧嶂无归日,一塌红尘有泪时。雕琢只应劳郢匠,膏肓终恐误秦医。浮生七十今三十,从此凄惶未可知。”诗人之“旅魂”开始怀疑自己偃蹇的穷困命运。
满川碧嶂是他乡的山水,归去无期是五湖的烟月,壮士断腕,英雄揾泪,苏奏枯槁,屈子憔悴。多么希望郢匠一斧,雕琢成材;多么担心秦医错过,不可救药。首句“憔悴长安”与末句“凄惶未知”相呼应,把现今的憔悴与未来的凄惶宿命扭结在一起,读来更让人觉得前程悲凉。
咸通九年(868年)春,38岁的罗隐又一次落第,铩羽而归江东。他自秦岭经商州过襄州一路南行,准备到曾经取解的南康郡(今江西赣州)造访亲故。路过钟陵(今江西南昌东南),熟悉的山水,又遇到了熟悉的云英,于是写下了著名的《嘲钟陵云英》诗:
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这首诗原载于五代何光远《鉴戒录》卷八《钱塘秀》中:“罗秀才隐,傲睨于人,体物讽刺。初赴举之日,于钟陵筵上与娼妓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经钟陵,复于云英相见。云英拊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矣?’隐虽内耻,寻亦嘲之:‘钟陵醉别十余春,重见云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当年从南康北上赶考路过钟陵,筵席上遇到年轻的歌妓云英,新荐进士的身份,自然使罗隐倍感风光,兼以初出茅庐,意气风发,当时定是豪气干云,极欢而别。十来年后再次见到云英,一纪赶考未脱白的现实,让罗隐多少有些尴尬。
云英的拊掌嘲笑,罗隐的反唇相讥,极具喜剧色彩,却多悲剧意味。 云英“掌上身”和一纪后尚“未嫁人”的对比,罗隐“未成名” 与当年第一次赶考路过钟陵,初遇云英时的落差,最后用“俱是不如人”点破,谑笑中的辛酸,落泊中的叹息,个中的滋味,或许只有他们才能品悟。
从38岁(咸通十一年)到55岁(僖宗光启三年),除了战乱和灾荒之外,罗隐不是在长安参加考试,就是在参加考试的路上。素有江东才子、满腹经纶之称的罗隐,为什么总是累举不第呢?
一首《感弄猴人赐朱绂》诗,淋漓尽致地揭露出唐末用人制度的荒唐:“十二三年就试期,五湖烟月奈相违。何如学取孙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绯。”
《幕府燕闲录》载,在唐昭宗逃难的路上,随驾艺人只有弄猴者。猴颇驯,能随班起居。昭宗赐以绯袍,号孙供奉。按唐制,五品官服浅绯,四品官服深绯。一个装腔作势的耍猴人,居然能赐以大官的朝服,封以皇帝近侍的官衔,而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十二三年背井离乡上京考试,竟一无所得!
黑暗的社会现实及多年应举的心理压力和类遭黜落的精神打击,帮助罗隐从自我迷失的幻想中彻底解脱出来,遂有《归五湖》诗:“江头日暖花又开,江东行客思悠哉。高阳酒徒半凋落,终南山色空崔嵬。圣代也知无弃物,侯门未必用非才。一杆明月一竿竹,家住五湖归去来。”此后,他带着近30年未曾实现的科举梦,绝意朝廷,回归江东。
生于唐末乱世,备尝离乱之苦的罗隐,对朝代的兴衰枯荣表现出特殊的敏感性。他的咏史诗常以独特视角,来审视王朝的更替,在咏叹和议论历史成败得失中,寄寓着对现实的讽刺。如《筹笔驿》: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
筹笔驿,古驿名,在今四川广元市北,诸葛亮出师曾驻军筹划于此。诗歌首先叙写了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复兴汉室,而离开隐居的南阳,历事两朝,运等帷幄,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然后,又指出了诸葛亮开始的成功和后来的失败,都与客观形势即“时”与“运”分不开。
接着,说蜀汉江山来之不易,却轻易断送在后主刘禅和庸臣谯周之手,实在可惜。最后以写景作结,既昔日的驿站尘封已久,诸葛亮的功绩也逐渐被世人遗忘,唯有山下的流水似乎情意绵绵,依旧傍着驿站流淌。
该诗的章法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关键在于“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的警句,说的是一个人在时运顺遂时,仿佛连天地都帮助他;若时运不济,就连英雄人物也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清晰地阐明了“时世”与“英雄”的辩证关系,进而揭示出“时世造就英雄”的历史规律。其实,《筹笔驿》这首诗,罗隐名为咏史,实则是对自己一生怀才不遇的酸楚感叹。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历史的镜子常能照出现实的影子。罗隐的咏史诗,也明显地染上了唐末的时代色彩。他很少吟咏经纶盖世、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揆天则地、气势浩然的盛世景象,而多感于亡国之君和末世之时。
因此,他的咏史诗,除了强烈的讽刺意味,还有浓厚的悲凉气氛。吴王夫差是臭名昭著的亡国之君,罗隐在《姑苏台》中写道:“让高泰伯开基日,贤见延陵复命时。未会子孙因底事,解崇台榭为西施。”
周太王的长子泰伯,为了让位给弟弟季历(周文王的父亲)而逃到吴地,吴国就在这样高尚的禅让中开基。后来,吴公子季札(延陵季子)历聘上国,遍交贤士,被大家称为贤能之人。
可是,子孙后代却没有继承前辈的好传统,为西施大造楼台亭榭,寻欢作乐,导致了国家的灭亡。隋炀帝也由于荒淫无度,“君王忍把平陈业,只博雷塘数亩田”,这里有着多少深刻的教训啊。
除了吴王夫差和隋炀帝,罗隐甚至连本朝的玄宗和昭宗也敢讽刺,而且流传很广。如《华清宫》:
楼殿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
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
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骊山华清宫避寒,过着荒淫无度、穷奢极欲的生活。君王也知晓道德上要超过尧舜,怎奈要杨贵妃高兴才行!直言刺世,讽刺昏君荒淫误国。因为《华清宫》这首诗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直接导致执政者的不满。
据史料记载:“昭宗欲以甲科处之,当场有大臣奏曰:‘隐虽有才,然多轻易,明皇圣德,犹横遭讥谤,将相臣僚,岂能免乎凌轹?’帝问讥谤之词,对曰:‘隐有《华清宫》诗曰:楼台层层佳气多,开元时节好笙歌。也知道德胜尧舜,争奈杨妃解笑何。其事遂寝’”
罗隐不是一个“女祸亡国”论者。他认为,世事的变迁、国家的兴亡都是时势所然,怎么能把亡国的罪责横加在几个女子身上呢?于是,他为我国古代那些蒙受亡国罪责的女人大翻旧案。这在《西施》一诗中有明确的表现:“家国兴亡自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倾吴国,越国亡来又是谁?”
如果说吴国灭亡是西施造成的,那么促使越国灭亡的又是谁呢?雄辩的历史事实,严密的逻辑推理,既是对那些“女人祸国”论者的当头棒喝,又是对那些为统治阶级开脱亡国之罪的辛辣讽刺。
当唐末农民起义军进入长安时,唐僖宗仓皇逃向四川。平定起义之后,僖宗又回到长安,路上又经马嵬坡,罗隐作《帝幸蜀》:“马嵬山色翠依依,又见銮舆幸蜀归。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
谢阿蛮是新丰市的女伶,很受杨贵妃宠爱,诗歌借她的口吻,不仅挖苦唐玄宗在安史之乱时让杨贵妃当替罪羊,而且逼问唐僖宗:你逃奔四川,还有什么藉口可找呢?
罗隐的咏物诗,同我国古代大部分咏物诗一样,均有所寄托。或借物言志,或借物说理,或借物刺世,或借物遣兴。无论哪种题材,都能卒章显志,比兴自如。如《病骢马》:
枥上病骢蹄袅袅,江边废宅路迢迢。
自经梅雨长垂耳,乍食菰浆欲折腰。
金络衔头光未灭,玉花毛色瘦来焦。
曾听禁漏惊街鼓,惯踏康庄怕小桥。
夜半雄声心尚壮,日中高卧尾还摇。
龙媒落地天池远,何事牵牛在碧霄?
其中“夜半雄声心尚壮,日中高卧尾还摇”一句,蕴涵着病中骏马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凄怆情怀;而前4句梅雨季节身处“江边废宅”、菰浆充饥、双耳低垂的“枥上病骢”形象,与“曾听禁漏惊街鼓,惯踏康庄怕小桥”尊贵身影的强烈对比,“金络衔头光未灭”与“玉花毛色瘦来焦”的色泽反差,以及末句对于骢马落地而牵牛在天的反常情形的反诘,无一不使人为病骢之宏迈志向和落寞处境而浩叹悲歌。《病骢马》题目本身,已清晰地表明了诗人对骢马的同情;而当把这首诗理解为以物喻人的作品时,这份同情便成了饱含愤愤不平的自怜。
在咏物诗中,比较多的还是罗隐借物讥讽、鞭挞现实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他借咏钱揭露朱门富户虎狼般的贪婪本性,“朱门虎狼性,一半逐君回”。《金钱花》一诗,对这种残暴贪黩行为挖苦得更为尖刻:“占得佳名绕树芳,依依相伴向秋光。若教此物堪收贮,应被豪门尽劚将。”那黄灿灿的金钱花如能像金钱一样收藏起来,也将会被豪门砍尽采光,这是多么辛辣的讽刺。
《鹰》是对那些爬上高位的既得利益者的剖视:“越海霜天暮,辞韬野草干。俊通司隶职,严奉武夫官。眼恶藏蜂在,心粗逐物殚。近来脂腻足,驱遣不妨难。”那些如同司隶、武官一样的苍鹰,脂足肚饱之后,就不肯尽职,连主人驱遣都不容易了。这让人想起那些随着地位变化而忘乎所以,甚至大摆架子、养尊处优的庸官俗僚。
罗隐的笔触,还指向更广大的贫困者。一首咏《雪》诗,揭示了咫尺相异的现实:
尽道丰年瑞,丰年事若何?
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多!
丰收了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被统治者盘剥得更多。在大雪纷飞中,有多少求告无门的贫者将冻饿而死。对他们来说,大雪,与其说“瑞”,还不如说“灾”,还是不要太多为好。将深沉的愤慨寓于冷隽的讽刺之中,既是对深居大宅、锦衣玉食的富户显贵高谈阔论的揶揄,也是对丰歉同悲者的同情,还有自己连年奔波却寒饿相接的不平。
除了咏怀、咏史和咏物诗以外,罗隐还有不少写景诗和酬赠诗等,也是清词丽句,传遍时人之口。在那风雨飘摇的时代,曲折坎坷的经历,加上傲岸不屈的性格,使罗隐的诗充满了浩然之气,“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因此,他的诗能跨越时代,受到古今中外文人雅士的好评。
二
罗隐在应举之初即有诗名,他不仅得到过大唐宰相令狐绹、李藯等人的赏识,在朝廷内外也有相当的影响。到了咸通乾符年间,罗隐的诗更是远近闻名。
令狐绹对罗隐诗歌的喜好,竟然超过对其子令狐滈进士中举的喜悦。《十国春秋》卷八四载,令狐绹子滈进士及弟,罗隐写诗祝贺。令狐绹对他儿子说:“我不喜汝及第,喜汝得罗公一篇耳。”
罗隐的宗人罗袞出使吴越时赠给罗隐诗中有“寰区叹屈瞻天问,夷貊闻诗过海求”的句子,可见当时罗隐在海外(主要是朝鲜和日本)的名声了。
就是明清时期的小说家们,也常引用他的诗句。在《西湖二集》《金瓶梅词话》《拍案惊奇》等书中,都曾引用《雪》《偶兴》《自谴》等诗。总之,罗隐虽然算不上唐代诗坛巨擘,但他的诗歌以辛辣的讽刺性、明显的哲理化和浅切的通俗语言,在晚唐诗歌发展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且形成了鲜明的艺术个性。
如果说“缘情必务于刺时,体物勿忘于谏猎”是罗隐诗歌创作的主要特色,那么,直言刺世或委婉暗讽,则是他诗歌创作的基本风格。罗隐出身于官宦之家,有满腔的政治抱负和才华。然而,生逢乱世,十举不第,仕途坎坷,对社会现实极度不满。
《唐才子传》卷九称其“自以为当得大用,而一第落落,传食诸侯,因人成事,深怨唐室。”再加上其“性简傲,高谈阔论,满座生风。好谐谑,感遇辄发……”的思想性格,言词激切、直陈时弊,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如《燕昭王墓》:“浮世近来轻骏骨,高台何处有黄金?思量郭隗平生事,不殉昭王是负心。”感叹世上再无燕昭王筑黄金台招揽人才,唯见黄钟遭弃,瓦缶争鸣,讽刺的锋芒直指当朝的昏君佞臣。又如《后土庙》:“四海兵戈尚未宁,始于云外学仪形。九天玄女犹无圣,后土夫人岂有灵?”淮南节度使高骈在战火四起中不理军政,迷信方士,酷好仙术,罗隐潜题《后士庙》刺之,因此激怒了高骈,差点丢掉性命。
其实,罗隐更不乏比兴兼用、谐谑暗讽的诗。如《台城》:“水国春长在,台城夜未寒。丽华承宠渥,江令捧杯盘。宴罢明堂烂,诗成宝炬残。兵来我有计,金井玉钩栏。”陈后主沉湎酒色,不理朝政,最终导致荒淫误国的可悲下场。
然而,诗歌并没有用愤激的言词指着陈后主的鼻子大骂,而用浅显的语句冷峻描述一些历史画面,甚至用“兵来我有计,金井玉钩栏”这类调侃的诗句摹拟陈后主的话,幽默滑稽,寓庄于谐。
然而,细细品味诗意,在貌似冷静的描述和漫不经心的谈论中,又寄寓着诗人心中的忧愤和无奈。在《铜雀台》一诗中,罗隐用“只合当年伴君死,免教憔悴望西陵”的反语形式,真实地道出了铜雀台的妾伎们生不如死的悲惨命运。尽管诗歌写得十分含蓄,其中所蕴涵的愤世嫉俗与饱含血泪的无声控诉力透纸背,达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
用语浅近,道理深邃,是罗隐诗歌的又一大特点。罗隐大半辈子穷困潦倒,与社会下层接触较多,其通俗明快和诙谐幽默的诗歌语言与此不无关系。如“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觉老从心头来”“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明年更有新条在,绕乱春风卒未休”“芳草有情皆碍马,好花无处不遮楼”等。
这些通俗明了、几近口语的诗歌,传唱范围之广,影响之大,已深深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
难能可贵的是,罗隐不从时俗,直接承继了中唐“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的诗学理论,“言者不期枝叶而贵在达情”,开创了清新质朴、简洁明快的一路诗风。如《京中正月七日立春》诗:“一二三四五六七,万木生芽是今日。远天归雁拂云飞,近水游鱼迸砅出。”该诗只是简单描绘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归雁从远处飞来,游鱼迸砅而出的景象。然而,在这平实的话语之中,又寄寓了诗人在新的一年里多少的希望和期待呢?
在晚唐,社会的动荡,朝廷的没落,以及诗人对科举追求的失败,进而引发的对历史、对现实以及对人生的深沉反思,势必在诗歌中体现出来。
如《黄河》:“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故难明。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诗人认为,浑浊的九曲黄河似乎包含着难以明了的天意,任你倾倒多少阿胶都不能够把它澄清,它的浑浊自有渊源,它的曲折更是必然。既然才出昆仑便不清,我们又怎能凭一己之力去改变它呢?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级。
再如《秦纪》:“长策东鞭及海隅,鼋鼍奔走驱鬼神。怜君未到沙丘日,肯信人间有死无。”像秦始皇那样伟大的历史人物,为了东巡耗费了那么大的财力物力,可惜还未到沙丘,便死在路途之中,其结局不是和普通人一样,生老病死,殊途同归,还让我们怎么怀疑“肯信人间有死无”。
罗隐是现实的,又是超凡的。在他谐谑讥刺的诗歌中,无不展示出睿智冷静的思考,以及对国家、对黎民的眷眷情怀。他担心“雨夜老农伤水旱”,反对“也是须供使宅鱼”的民生观;他关心时政,心系朝廷,所秉持的“陪臣无以报,西望不胜情”“静怜贵族谋身易,危惜文皇创业难”的国家观,“有其位则执大柄以定是非,无其位则著私书而疏善恶”的使命观,仍给我们从善向上的动力,并呈现出穿越时空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经过岁月的冲洗和历史的沉淀,今天再读罗隐诗,更觉得光芒四射与荡气回肠。
图①罗隐画像
②山舍竹林
■许双福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