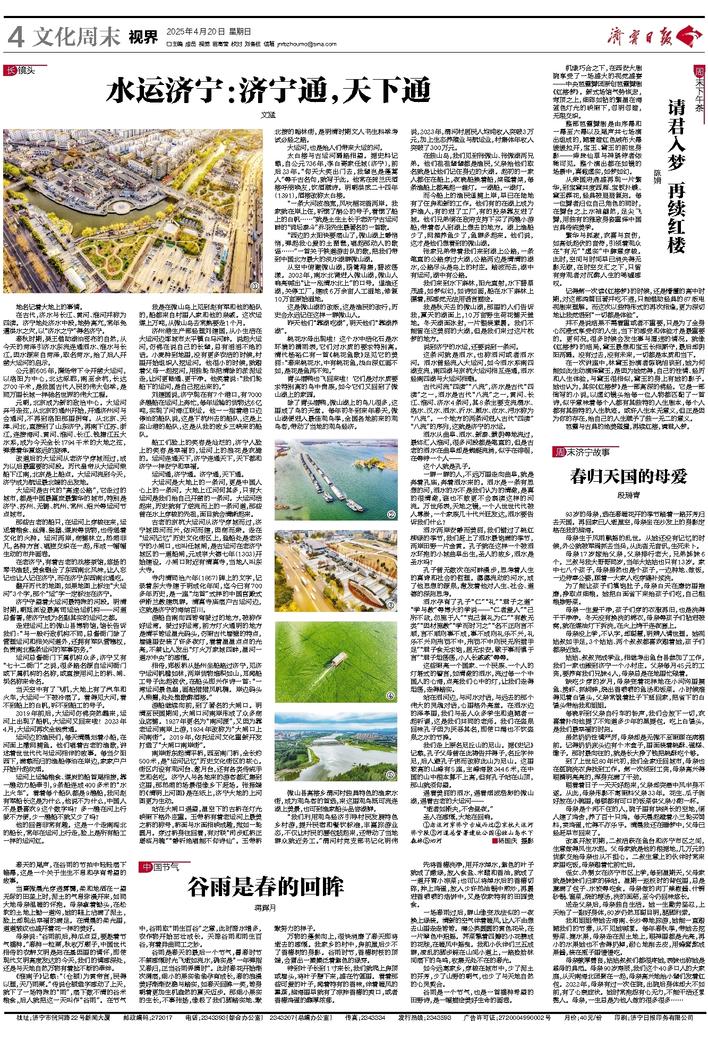93岁的母亲,选在春暖花开的季节踏着一路芬芳归去天国。再回家已人逝屋空,母亲坐在沙发上的身影定格在我的脑海。
母亲生于风雨飘摇的乱世。从她还没有记忆的时候,外公就被军阀抓去当兵,从此杳无音讯,生死未卜。
母亲17岁嫁给父亲,父亲排行老大,兄弟姊妹6个。三叔与我大哥哥同岁,当年大姑姑也只有13岁。家中七八个孩子,母亲虽然也是个孩子,一边种地、做饭,一边侍奉公婆,顾着一大家人吃穿缝补浆洗。
为了能让孩子们填饱肚子,母亲白天在磨坊里推磨,挣取点细粮。她把白面省下来给孩子们吃,自己粗粮掺野菜。
母亲一生爱干净,孩子们穿的衣服再旧,也是洗得干干净净。冬天没有换洗的棉衣,母亲等孩子们钻进被窝,就在煤油灯下拆洗,在火上烤干连夜套上。
母亲没上学,不认字,却聪慧,明辨人情世理。她视姑叔如手足,3个姑姑、两个叔叔都喜欢跟着她,孩子们都亲近她。
姑姑、叔叔完成学业,相继考出鱼台县参加了工作,我们一家也搬到济宁一个小村庄。父亲每月45元的工资,要养育我们兄妹4人,母亲总是在地里忙碌着。
缺吃少穿的岁月,母亲变着花样地在小河沟里摸鱼、捞虾、抓蚵蚌,烧出香喷喷的鱼汤和饭菜。小时候难得见着白馒头,父亲常饿着肚子下班回家,把省下的白馒头带给我和姐姐。
每晚听到父亲自行车的铃声,我们会放下一切,欢喜着扑向他提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黑提包。吃上白馒头,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刻。
虽然奶奶性情严厉,母亲却是无微不至照顾在病榻前。记得奶奶床头边有个木盒子,里面装着桃酥、蛋糕、馓子。那时最向往的,就是长大挣了钱把桃酥吃个够。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全家迁回城市,母亲也在医院洗衣房找到工作。第一次领到工资,母亲高兴得眼睛明亮亮的,浑身充满了干劲。
眼看着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父亲却突患中风半身不遂。从此,母亲形影不离照料父亲33年。花生、瓜子剥好放在小碗里,每顿都有可口的饭菜供父亲小酌一杯。
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院子里有块狭长的空地,俩人建了鸡舍,养了百十只鸡。每天晨起蹬着小三轮买饲料,卖鸡蛋,忙得不亦乐乎。清晨我还在睡梦中,父母已经赶早市回来了。
改革开放初期,二叔活跃在鱼台和济宁市区之间,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父母家就是他的根据地,几万元的货款交给母亲也从不担心。二叔生意上的伙伴时常来家里吃饭,母亲跟着忙前忙后。
侄女、外甥女在济宁市区上学,每到星期天,父母家就是妹妹们归家的驿站。星期一返校时的背包里,总是塞满了包子、水饺等吃食。母亲做的肉丁辣椒酱、什锦砂锅、馏菜,烧的粳汤,洗的面筋,至今仍回味悠长。
送走父亲后,母亲独自生活。她一生勤劳坚忍,上天给了一副好身体,80岁仍然耳聪目明,腿脚利索。
我和姐姐带她去海南、长沙等地旅游,她能一直跟随我们的节奏,从不见她喊累。每年春秋季,带她去挖野菜、摘水果,母亲走在泥土地上,眼神里都是光亮,再小的水果她也不舍得扔掉,耐心地削去皮,用蜂蜜熬成果酱,装在瓶子里慢慢吃。
母亲敦厚善良,姑姑叔叔们都很疼她,表妹也称她是慈母的典范。母亲90岁寿辰,我们这个40多口人的大家庭,从天南海北团聚在一起,母亲高兴地给小辈们发着红包。2022年,母亲有过一次住院,出院后身体却大不如前,有了心衰症状。她时常抱怨有心无力,不能干活还累赘人。母亲,一生总是为他人做的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