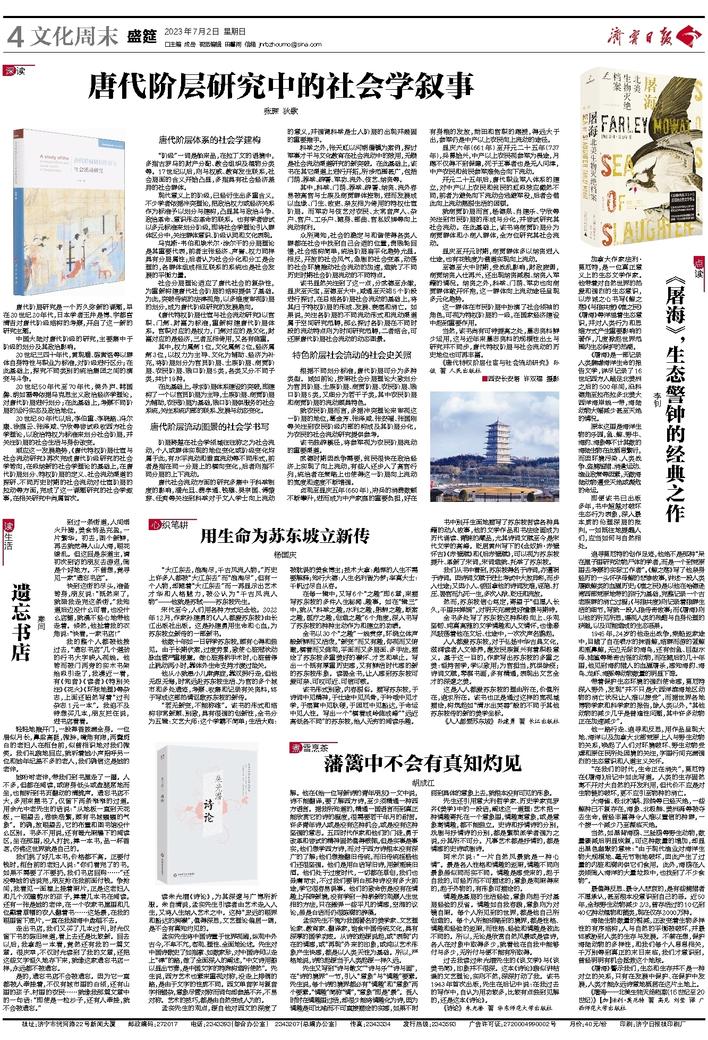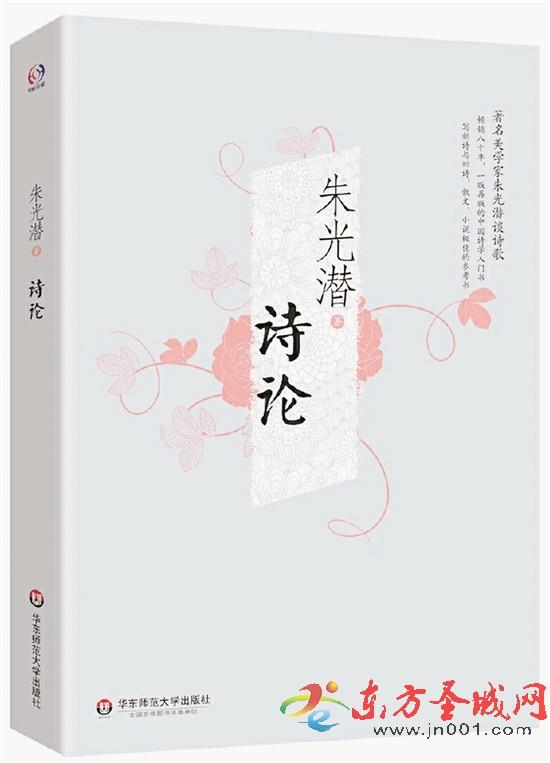读朱光潜《诗论》,为其深邃与广博所折服。朱自清说,孟实先生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这种“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值得深思,文艺理论偏居一隅,是不会有真知灼见的。
孟实先生将中国诗置于世界视阈,纵观中外古今,不卑不亢,客观、理性、全面地论述。先生对中国诗歌史了如指掌、如数家珍,对中国诗何以走上“律”的路,做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中文诗用韵以显出节奏,是中国文字的特殊构造所使然”。先生说,西方艺术也素来重视对称,没走上排偶的路,是由于文字的性质不同。西文单音字与复音字相错杂,意象尽管对称而词句却参差不齐,不易对称。艺术的技巧,都是由自然变成人为的。
孟实先生的观点,源自他对西文的深度了解。他在《给一位写新诗的青年朋友》一文中说,诗不能翻译,要了解西方诗,至少须精通一种西方语言。据我所知道的,精通一国语言而到真正能欣赏它的诗的程度,很需要若干年月的耐苦。许多青年诗人或是没有这种机会,或是没有这种坚强的意志。五四时代作家和他们的门徒,勇于改革和尝试的精神固然值得敬佩,但是实事是事实,他们想学西方诗,而对于西方诗根本没有深广的了解;他们想推翻旧传统,而旧传统桎梏他们还很坚强。他们是用白话写旧诗,用新瓶装旧酒。他们处于过度时代,一切都在草创,我们也毋庸苛求,不过我们要明白那种诗没有多大前途,学它很容易误事。他们的致命伤是没有在情趣上开辟新境,没有学到一种崭新的观察人生世相的方法,只在搬弄一些平凡的情感,空洞的议论,虽是白话而仍很陈腐的辞藻。
孟实先生不愧为我国著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家,饱食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从诗的起源说起,或“表现”内在的情感,或“再现”外来的印象,或纯以艺术形象产生快感,都是以人类天性为基础。所以,严格地说,诗的起源当于人类起源一样久远。
先生又写到“诗与散文”“诗与乐”“诗与画”,在“诗的境界”一节,引入“意象”与“情趣”要素。先生说,每个诗的境界都必有“情趣”和“意象”两个要素。“情趣”简称“情”,“意象”即是“景”。吾人时时在情趣里过活,却很少能将情趣化为诗,因为情趣是可比喻而不可直接描绘的实感,如果不附丽到具体的意象上去,就根本没有可见的形象。
先生还引用意大利哲学家、历史学家克罗齐《美学》中的一段话,阐述这一道理:艺术把一种情趣寄托在一个意象里,情趣离意象,或是意象离情趣,都不能独立。史诗和抒情诗的分别,戏剧与抒情诗的分别,都是繁琐派学者强为之说,分其所不可分。凡事艺术都是抒情的,都是情感的史诗或剧诗。
阿米尔说:“一片自然风景就是一种心情”。景是各人性格和情趣的返照,情趣不同则景象虽似同而实不同。情趣是感受来的,起于自我的,可经历而不可描述的;意象是观照得来的,起于外物的,有形象可描绘的。
情趣是基层的生活经验,意象则起于对基层经验的反省。情趣如自我容貌,意象则为对镜自照。每个人所见到的世界,都是他自己所创造的。每个人所能领略到的境界,都是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而性格、经验和情趣是彼此不同的。所以,无论是欣赏自然风景或是读诗,各人在对象中取得多少,就看他在自我中能够付与多少,无所付与便不能有所取得。
过去我读过朱光潜先生的《谈文学》与《谈美书简》,印象并不很深。这本《诗论》貌似讲枯燥的文艺理论,实则不然,深深打动了我。该书1943年首次出版,先生在后记中说:在我过去的写作中,自认为用功较多,比较有点独到见解的,还是这本《诗论》。
《诗论》 朱光潜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