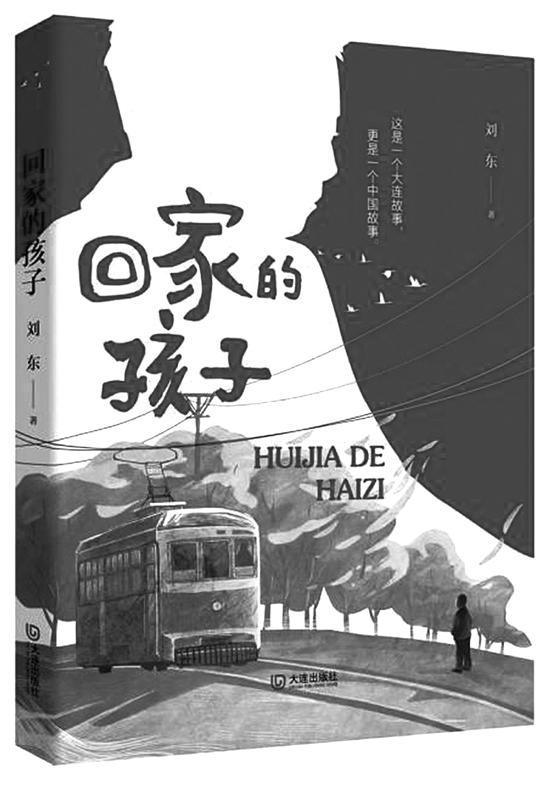(一)
《回家的孩子》是刘东从事文学创作三十几年来,第一部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作品,是首部正面表现大连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奴化教育时期中国青少年儿童不甘奴化与压榨的故事和精神面貌的儿童文学作品。
可以说,《回家的孩子》填补了一个题材空白,也是刘东文学创作生涯中一个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刘东此番文学性、纪实性和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的小说创作,显示了他艺术实践的自觉与人文担当。刘东说:“无论如何,让现在的孩子们有机会了解一段历史……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才是最重要的!”
在关于这部小说的创作谈中,刘东并不讳言他写作25年来,从念头的萌发,搜集、阅读资料,到访谈、动笔、搁笔,到再动笔之间的曲折。“就算是仅仅想把那些故事写好,也并不容易。那些故事除了在年代上离我久远,更重要的是,它们离我的感情、感受和感悟也很遥远。”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作家本人都遥远而疏离的往事,如何引起本世纪出生的中小学生的情感共鸣、认知和认同?这尤其显现出“旧事重提”的意义——让少年儿童通过文学阅读“经验”了解的史实,从文学作品中汲取成长的力量,激发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
尤其是当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与青少年读者同龄时,自觉的和下意识的比照,会对青少年产生影响,包括情感培育、行动判断、自我评价等等。所以,读完这部小说,我感到这部小说对青少年理智与情感的培养、价值观的确立等,都会发生作用。
这个浸染的作用如何发挥呢?刘东说:“一个无法打动我的故事,我是无法用它去打动我的读者的。”写好这部作品,他必须走进记忆,走进人心。他说,他要写的“不是一个落满了灰尘的隔世故事,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一颗颗鲜活的心。这些鲜活的人和心,会使那些遥远而陌生的故事,变得不再遥远,不再陌生,也会真正打动那些认真阅读这个故事的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一颗颗鲜活的心”。
如果说,这个认识上的突破,解决了刘东创作中遇到的瓶颈,那么从文学作品的接受来说,正是《回家的孩子》中人物的鲜活——包括生动的个性的对话、行动和思想情感,与年龄、性格、认知、生存环境的和谐一致——使事、物、情、理、意,得以在起伏跌宕的情节中生动彰显,从而让青少年读者能够走近历史语境,进入人物内心世界,在感同身受中被怡情、培智和化育。
(二)
《回家的孩子》十七章两个主线,围绕唐生和田仲男两个青少年儿童人物展开故事情节,从多角度书写日本占领旅大期间的奴化统治,中国人对其的反抗。小说从抗日反侵略,民族、国家和精神独立为内涵的情节展开中讲故事,展现青少年在抗日战争背景下,特殊环境中的心智状态及其发展,展现家国情怀、家仇国恨在青少年成长中的励志和启蒙及精神支撑与影响,展现人性大爱中中日两个民族中善良的人之间的互相帮助,等等。
全书构架精巧而沉稳,情节设计与小说语言艺术的结合,令虚构现实的真实性使文本所讲的故事更加真实,所以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吸引读者——文学家要通过大胆的虚构,揭示他们的想象力所能接近的真理和价值。
小说《回家的孩子》书名的含义,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层层递进:从第一章唐生回家,因日本人的统治和压迫而不能认祖归宗,田仲男水涧堡事件后回家历经的磨难,到最后日本人在中国战场上的全线溃败与投降后,旅大地区回到祖国的怀抱——当然“山蕲堂”也要改名为“当归堂”。
在这个“回家”概念中,作家展现了外族入侵时隐姓埋名的无奈与屈辱和国家独立从而人才能独立,才能扬眉吐气地活着的真理。反对侵略,为民族和国家独立而战,才会有家家户户的稳健的生活,才没有妻离子散,才有自由温暖的学习环境——作家一步步将道理展现为青少年儿童可以直观感受到的家庭氛围、学习环境、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教育内容等叙事中,使今天的青少年儿童,从具体中推理和联想那个年代的苦难深重,斗争的意义,牺牲者的奉献精神和信仰追求的意义,进而在今天流行文化与消费主义的盛行中,对青少年儿童的价值追求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唐生和仲男为代表的青少年儿童,是值得赞颂的。
赞颂他们,是因为他们人小却爱国、爱家,懂民族大义。如果战争持续下去,他们是会像伯男一样,奔赴战场,为民族为国家而战的;赞颂他们,还因为他们是代表为生存而斗争的全体中国人民——比如,作家多次在细末之处写到了前线战士的英勇,田伯男就是其中之一。
另一方面,战争爆发时,青少年儿童是应该被保护和免于摧残的,从而宋晓辉的害怕也是应该得到理解与同情的——少年儿童在社会中的脆弱性,本就使得他们极易受到伤害。
当战争发生,儿童没有“免战区”。野心勃勃地做着“关东州”千秋大梦的日本人,对中国少年儿童进行的剥夺自由的奴化教育,造成他们身份确立的成长困惑,并常常受到侮辱、歧视、责罚和体力劳动的盘剥,甚至剥夺他们年幼的生命。
“六一”国际儿童节设立的初衷,就是旗帜鲜明地声讨二战中法西斯势力杀害、奴役儿童的行为,并保护未来的儿童免受战争摧残。讲到这里,我想青少年儿童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学生阅读《回家的孩子》这部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时,是需要阅读指导的,此书深藏着反对侵略战争、热爱和平、冲破狭隘民族主义苑囿等深意。
《回家的孩子》中,“关东州”的儿童,是生存在受虐环境中的,对他们来说,成长是一项尤为艰巨的任务。将成长这个问题显赫地摆到少年儿童读者以及成人读者面前,是非常有意义的。无论什么时代、时期,或某个时刻,“我是谁”这个问题会决定一个人的判断、言行和选择。
“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最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自己是谁!现在,所有人都在心里大声地问问自己:我是谁?我是谁?” 这是一个终极的和终身的问题——小说的第十六章也就是倒数第二章,田映川说:“但愿日本人的牢房能让他(荣芳)明白,他到底是谁。”所以,“我是谁?”这个问题,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被提出,这体现了作家的良苦用心。
(三)
列夫·托尔斯泰认为,“为了使儿童热爱读书,必须让他们阅读易懂的和有趣的……趣味性乃是有益性和通俗性唯一的标志”,并且“儿童对真实的内容,对有艺术表现力的,或者有教益的内容的要求,比我们强烈得多”。刘东的这部《回家的孩子》像他的所有儿童文学作品一样,兼具了生动、易懂、有趣、艺术性与教益性相得益彰等文学素质。
鲜活的、代入感强烈的、符合小说中青少年儿童身份的对话语言,与对话过程中传神的人物动作描写,能够激发青少年儿童读者的阅读兴趣。比如,唐生和田叔男之间、田仲男和同学之间的对话等,有时是在情节中交代背景,有时是在情节中推动故事的发展,有时是在对话语言中塑造人物性情、展现人物品格、预告人物未来可能的行动。
有时这些对话语言甚至是戏谑的,但是它们“表面上是白话文,很浅的,实际上里面的思想是很深的”。阅读《回家的孩子》,青少年儿童读者不应该只停留在对这部小说的情节和“中心思想”的关注,还应该注重作家的文学语言,这对于提升他们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都是非常有益的。好的儿童文学作品,能够激发儿童的语言灵性。
当然,刘东文学语言的造诣,绝不只体现在对话语言中。再比如,这部小说篇章名称中的隐喻和象征,使得整部小说更加耐人寻味。当我读完整部作品,回头看这17个标题的时候,我感到它们既是“画龙点睛”中的“睛”,能让全文“飞腾”起来,也是“提纲挈领”中的“纲”。
“春寒”“心中的地图”“暗夜之火”“希望”“回家的孩子”等章节题目,不仅贴合故事情节,而且像飘起的意蕴的薄纱,一边笼罩一边散溢。刘东是诗意的——这部小说的结尾多么美啊:“远处有祈福的钟声响起。新的一年来到了。”
(四)
早有论者指出,刘东一直“努力去开掘青春成长中难以把握、难以命名的部分,因而他的作品就呈现了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少见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种开拓性、复杂性和丰富性,体现在刘东文学创作中视野的广度、探索的深度、体察的精细,以及发现的能力和文字表现的艺术中。
《回家的孩子》无疑从选材、主旨、立意、情节、谋篇到语言,都再次印证了,无论从以上哪个角度和维度来说,刘东都是一位造诣高深的作家。■毛毛 摄影
《回家的孩子》 刘东 著 大连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