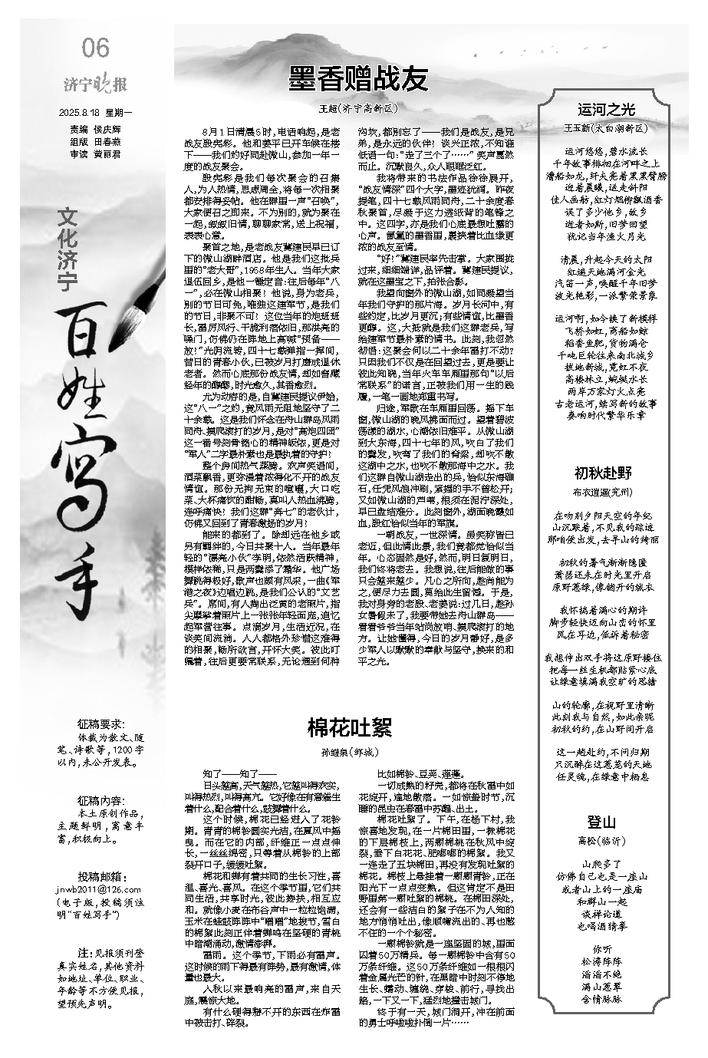王超(济宁高新区)
8月1日清晨5时,电话响起,是老战友殷宪彩。他和姜平已开车候在楼下——我们约好同赴微山,参加一年一度的战友聚会。
殷宪彩是我们每次聚会的召集人,为人热情,思虑周全,将每一次相聚都安排得妥帖。他在群里一声“召唤”,大家便召之即来。不为别的,就为聚在一起,叙叙旧情,聊聊家常,送上祝福,表表心意。
聚首之地,是老战友冀建民早已订下的微山湖畔酒店。他是我们这批兵里的“老大哥”,1958年生人。当年大家退伍回乡,是他一锤定音:往后每年“八一”,必在微山相聚!他说,身为老兵,别的节日可免,唯独这建军节,是我们的节日,非聚不可!这位当年的炮班班长,雷厉风行、干脆利落依旧,那洪亮的嗓门,仿佛仍在阵地上高喊“预备——放!”光阴流转,四十七载弹指一挥间,昔日的青春小伙,已被岁月打磨成退休老者。然而心底那份战友情,却如窖藏经年的醇醪,时光愈久,其香愈烈。
尤为动容的是,自冀建民提议伊始,这“八一”之约,竟风雨无阻地坚守了二十余载。这是我们怀念在舟山群岛风雨同舟、摸爬滚打的岁月,是对“高炮四团”这一番号刻骨铭心的精神皈依,更是对“军人”二字最朴素也是最执着的守护!
整个房间热气蒸腾。欢声笑语间,酒菜飘香,更弥漫着浓得化不开的战友情谊。那份无拘无束的喧嚷,大口吃菜、大杯痛饮的酣畅,真叫人热血沸腾,连呼痛快!我们这群“奔七”的老伙计,仿佛又回到了青春激扬的岁月!
能来的都到了。除却远在他乡或另有羁绊的,今日共聚十人。当年最年轻的“漂亮小伙”李明,依然活跃精神,模样依稀,只是两鬓添了霜华。他广场舞跳得极好,歌声也颇有风采,一曲《军港之夜》边唱边跳,是我们公认的“文艺兵”。席间,有人掏出泛黄的老照片,指尖摩挲着照片上一张张年轻面庞,追忆起军营往事。点滴岁月,生活近况,在谈笑间流淌。人人都格外珍惜这难得的相聚,畅所欲言,开怀大笑。彼此叮嘱着,往后更要常联系,无论遇到何种沟坎,都别忘了——我们是战友,是兄弟,是永远的伙伴!谈兴正浓,不知谁低语一句:“走了三个了……” 笑声戛然而止。沉默良久,众人眼眶泛红。
我将带来的书法作品徐徐展开,“战友情深”四个大字,墨迹犹润。昨夜提笔,四十七载风雨同舟,二十余度春秋聚首,尽凝于这力透纸背的笔锋之中。这四字,亦是我们心底最想吐露的心声。氤氲的墨香里,裹挟着比血缘更浓的战友至情。
“好!”冀建民率先击掌。大家围拢过来,细细端详,品评着。冀建民提议,就在这墨宝之下,拍张合影。
我望向窗外的微山湖,如同凝望当年我们守护的那片海。岁月长河中,有些约定,比岁月更沉;有些情谊,比墨香更醇。这,大抵就是我们这群老兵,写给建军节最朴素的情书。此刻,我忽然彻悟:这聚会何以二十余年雷打不动?只因我们不仅是在回望过去,更是要让彼此知晓,当年火车车厢里那句“以后常联系”的诺言,正被我们用一生的践履,一笔一画地郑重书写。
归途,军歌在车厢里回荡。摇下车窗,微山湖的晚风拂面而过。望着碧波荡漾的湖水,心潮依旧难平。从微山湖到大东海,四十七年的风,吹白了我们的鬓发,吹弯了我们的脊梁,却吹不散这湖中之水,也吹不散那海中之水。我们这群自微山湖走出的兵,恰似东海礁石,任凭风浪冲刷,紧握的手不曾松开;又如微山湖的芦苇,根须在泥泞深处,早已盘结难分。此刻窗外,湖面晚霞如血,殷红恰似当年的军旗。
一朝战友,一世深情。虽笑称皆已老迈,但此情此景,我们竟都觉恰似当年。心态固然是好,然而,明日复明日,我们终将老去。我想说,往后能做的事只会越来越少。凡心之所向,趁尚能为之,便尽力去圆,莫给此生留憾。于是,我对身旁的老殷、老姜说:过几日,趁孙女暑假未了,我要带她去舟山群岛——看看爷爷当年站岗放哨、摸爬滚打的地方。让她懂得,今日的岁月静好,是多少军人以默默的奉献与坚守,换来的和平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