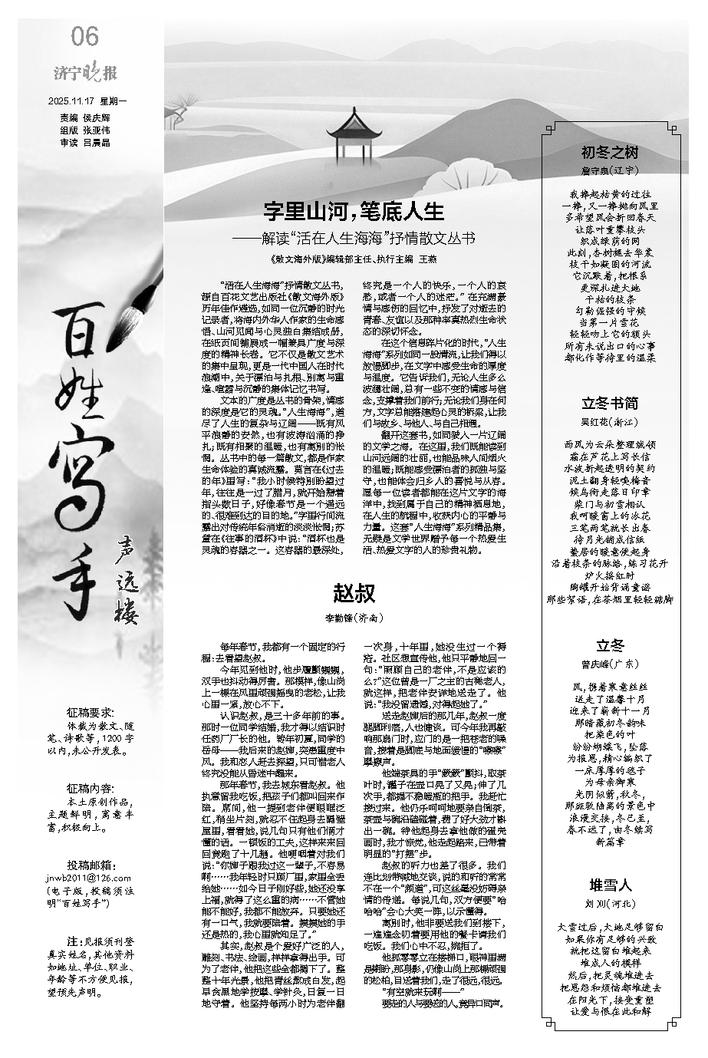李勤锋(济南)
每年春节,我都有一个固定的行程:去看望赵叔。
今年见到他时,他步履颤巍巍,双手也抖动得厉害。那模样,像山岗上一棵在风里顽强摇曳的老松,让我心里一紧,放心不下。
认识赵叔,是三十多年前的事。那时一位同学结婚,我才得以结识时任药厂厂长的他。转年初夏,同学的岳母——我后来的赵婶,突患重度中风。我和恋人赶去探望,只可惜老人终究没能从昏迷中醒来。
那年春节,我去城东看赵叔。他执意留我吃饭,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作陪。席间,他一提到老伴便眼眶泛红,稍坐片刻,就忍不住起身去隔壁屋里,看看她,说几句只有他们俩才懂的话。一顿饭的工夫,这样来来回回竟跑了十几趟。他哽咽着对我们说:“你婶子跟我过这一辈子,不容易啊……我年轻时只顾厂里,家里全丢给她……如今日子刚好些,她还没享上福,就得了这么重的病……不管她能不能好,我都不能放弃。只要她还有一口气,我就要陪着。摸摸她的手还是热的,我心里就知足了。”
其实,赵叔是个爱好广泛的人,雕刻、书法、绘画,样样拿得出手。可为了老伴,他把这些全都搁下了。整整十年光景,他把青丝熬成白发,起早贪黑地学按摩、学针灸,日复一日地守着。他坚持每两小时为老伴翻一次身,十年里,她没生过一个褥疮。社区想宣传他,他只平静地回一句:“照顾自己的老伴,不是应该的么?”这位曾是一厂之主的古稀老人,就这样,把老伴安详地送走了。他说:“我没留遗憾,对得起她了。”
送走赵婶后的那几年,赵叔一度腿脚利落,人也健谈。可今年我再敲响那扇门时,应门的是一把苍老的嗓音,接着是脚底与地面缓慢的“嚓嚓”摩擦声。
他端茶具的手“簌簌”颤抖,取茶叶时,罐子在壶口晃了又晃;伸了几次手,都握不稳暖瓶的把手。我赶忙接过来。他仍乐呵呵地要亲自倒茶,茶壶与碗沿磕碰着,费了好大劲才斟出一碗。待他起身去拿他做的蛋壳画时,我才惊觉,他走起路来,已带着明显的“打摆”步。
赵叔的听力也差了很多。我们连比划带喊地交谈,说的和听的常常不在一个“频道”,可这丝毫没妨碍亲情的传递。每说几句,双方便要“哈哈哈”会心大笑一阵,以示懂得。
离别时,他非要送我们到楼下,一遍遍念叨着要用他的餐卡请我们吃饭。我们心中不忍,婉拒了。
他孤零零立在楼梯口,眼神里满是期盼,那身影,仍像山岗上那棵顽强的松柏,目送着我们,走了很远,很远。
“有空就来玩啊——”
要走的人与要送的人,竟异口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