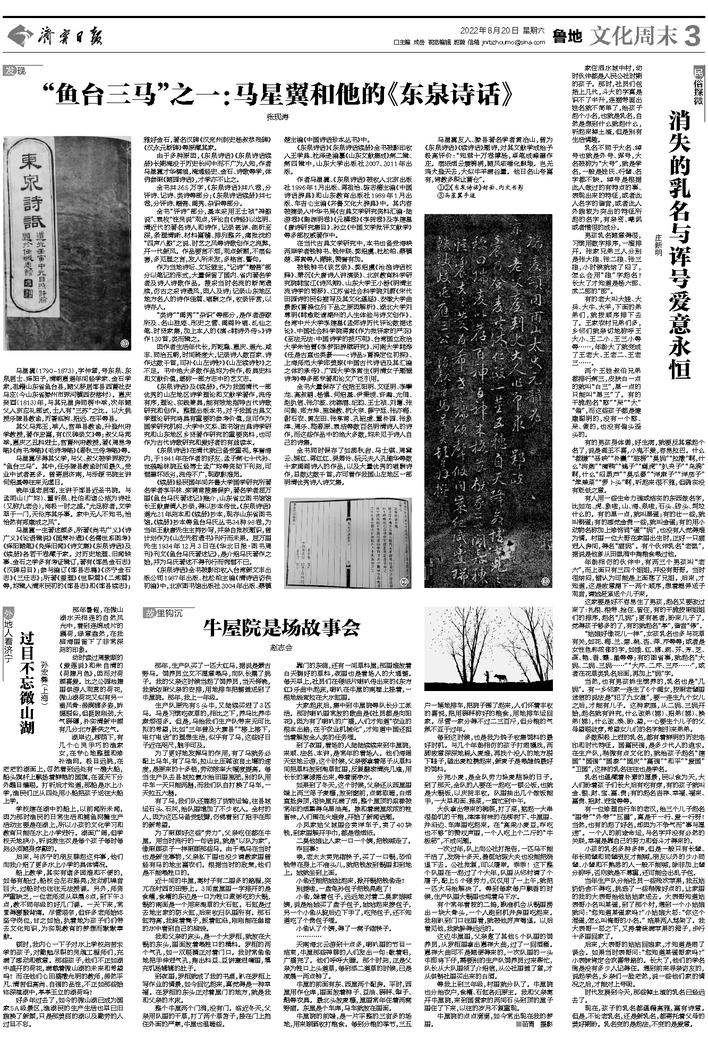那年,生产队买了一匹大红马,据说是蒙古野马。饲养员立文不愿意喂马,向队长撂了挑子。我的父亲这时候当起了饲养员,当天傍晚,我就依照父亲的安排,用地排车把铺盖送到了牛屋院。那年,我上一年级。
生产队原先有5头牛,又陆续买进了3匹马。马是习惯吃夜草的,相比之下,养马比养牛麻烦很多。但是,马给我们生产队带来无可比拟的希望,比如“三年普及大寨县”“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理想生活,似乎有了马,这些好日子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为了更好地发挥马的作用,有了马就务必配上马车,有了马车,拉山土压碱改良土壤的速度,是原来的十多倍,劳动效率大幅度提高。每当生产队去县城拉氨水给田里施肥,别的队用牛车一天只能两趟,而我们队自打换了马车,一天拉五六趟。
有了马,我们队还搞起了货物运输,往县城运石头、石灰,给队里增加了不少收入。全村的人,因为这匹马备受鼓舞,仿佛看到了招手在即的新希望。
为了照顾好这些“劳力”,父亲吃住都在牛屋。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说,就是“以队为家”,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那些马。由于喂马在当时也是新生事物,父亲私下里也没少请教家里曾经有马的地主富农们。根据当时的政策,他们是不能喂牲口的。
近十间的牛屋,离村子有二里多的路程,突兀在村西的田野上。3间堂屋里一字排开的是食槽,食槽的东边是一口为牲口煮粥吃的大锅,锅的南面是一个用来淘草的大石缸。石缸是过去地主家的防火缸,后来收归队里所有。那石缸特高,我踩着凳子,扳着缸沿,刚刚能在幽暗的水中看到自己的脑袋。
我和父亲的床头,是一个大罗柜,就放在大锅的东头,里面放着喂牲口的精料。罗柜的两个气孔,如一双眼睛正对着门口。我时常偷偷地把手伸进气孔,掏出料豆、豆饼塞进嘴里,填充饥肠辘辘的肚子。
到夜里,罗柜就成了我的书桌,趴在罗柜上写作业的情景,如今回忆起来,真觉得是一种幸福。在罗柜的东头正对着屋门的地方,就是我和父亲的木床。
整个牛屋两个门洞,没有门。临近冬天,父亲用队里的干草,打了两个草笘子,挂在门上挡住外面的严寒,牛屋也温暖些。
靠门的东侧,还有一间草料屋,那里堆放着白天铡好的草料,夜里也是看场人的大通铺。每天早上,社员们在硬纸片喇叭传出来的《东方红》乐曲中起床,喇叭在牛屋的南墙上挂着,一根地线耷拉在大水缸里。
大家起床后,集中到牛屋院等队长分工派活。那时喇叭里常放的歌曲是《社员都是向阳花》,因为有了喇叭的广播,人们才知道“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农业机械化”,才知道中国还担当着解放全人类的任务哩。
到了夜里,看场的人陆陆续续来到牛屋院,来顺、法名、本讲,是常年的看场人。他们海阔天空地云游,这个时候,父亲要拿着筛子从草料间把草料放到淘草缸里,反复翻滚清洗几遍,用长长的罩滤搭出来,等着滴净水。
如果到了冬天,这个时候,父亲还从西屋里端上两三筛子麦糠,放到窗前,点燃取暖,白烟直抵房顶,很快屋充满了烟,整个屋顶的梁椽被常年的烟熏得乌黑油亮。掺和着满屋浓浓的牲畜味,人们围在火堆旁,开始了新闻话题。
小凤家姑父城里会卖洋车子,卖了40块钱,到家里解开手巾,都是卷烟纸。
二臭他娘让人家一口一个姨,把钱喊走了。
咋回事?
唉,老太太卖完猪秧子,买了一口锅,恐怕钱带在身上不准头儿,就把钱放到锅里扣到地上。她就坐到上面。
小偷还能把她扯起来,掀开锅把钱偷走?
别提啦,一盘龟孙包子把钱晃跑了!
小偷,端着包子,远远地对着二臭家娘喊姨,说是给她买了盘子包子,她站起来接包子,另一个小偷从腚后边下手了,吃完包子,还不知道吃了个贵包子哩。
小偷认了个姨,得了一窝子猪秧子。
…………
天南海北云游到十点多,喇叭里的节目一结束,牛屋那些神聊的人们发出一句:歇着吧,广播完了。他们呼呼大睡。那个时刻,正是父亲为牲口上头道草,每到添二道草的时候,已是凌晨一两点钟了。
牛屋的前面有东、西屋两个配房。平时,西屋用作仓库,里面放着种子、豆油、磅秤、犁子、耙等农具。最北头放麦糠,屋里常年住着两窝野猫。东屋是个车库,马车就放在里面。
牛屋院的前端,是一片平整的三亩多的场地,用来晾晒收打粮食。每到分粮的季节,三五户一辆地排车,把院子围了起来,人们怀着丰收的喜悦,把用磅秤称好的粮食,用地排车运回家。尽管一家分得不过二三百斤,但分粮的气氛不亚于过年。
每到这时候,也是我为鸽子收集饲料的最好时机。与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打闹嬉戏,两脚故意深深地踩入麦堆,再找个没人的地方脱下鞋子,磕出麦粒攒起来,新麦子是喂雏鸽最好的饲料。
分完小麦,是全队劳力垛麦秸垛的日子。到了那天,全队的人要在一起吃一顿公饭,也就是大锅饭,以庆贺丰收。队里抽出几个做饭能手,一大早和面、择菜,一直忙到中午。
大伙拿出带来的碗筷,打了菜,掂起一大串很垫饥的干粮,津津有味的在柳树下、牛屋里、井沿边、车库里吃起来。在“高粱小麦豆,咋吃也不够”的赞叹声里,一个人吃上个二斤的“牛板筋”,不成问题。
一次过年,队上向公社打报告,一匹马不能干活了,发烧十多天,兽医站陈大夫也没能把烧退下去。公社批复,可以屠宰。乖乖!这下整个队里在一起过了个大年,队里从邻村请了个屠子,配上5个硬劳力,仅仅用了一上午,就把一匹大马给解决了。等到每家每户飘香的时候,生产队里大锅里也炖着马下水。
有个常年看坡的二捣,瞅准机会从锅里捞出一块大骨头,一个人跑到机井房里吃起来。我刚趴到门口往里看,就被他厉声喝退。以后看见他,我就躲得远远的。
这边牛屋里,父亲邀了其他5个队里的饲养员,从罗柜里拿出嘉祥大曲,过了一回酒瘾。嘉祥大曲可不是随便得来的,一次队里的一头牛即将下仔,需要别的生产队饲养员过来帮忙,队长从大队里领了介绍信,从公社里盖了章,才从供销社里买出来的白酒。
等我上到三年级,村里就分队了。牛屋院也分给农户,食槽、石缸各归原主。我和父亲离开牛屋院,来到国营家的两间石头到顶的屋子里住了下来,以往的岁月不复重现。
牛屋院的点点滴滴,如今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苗青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