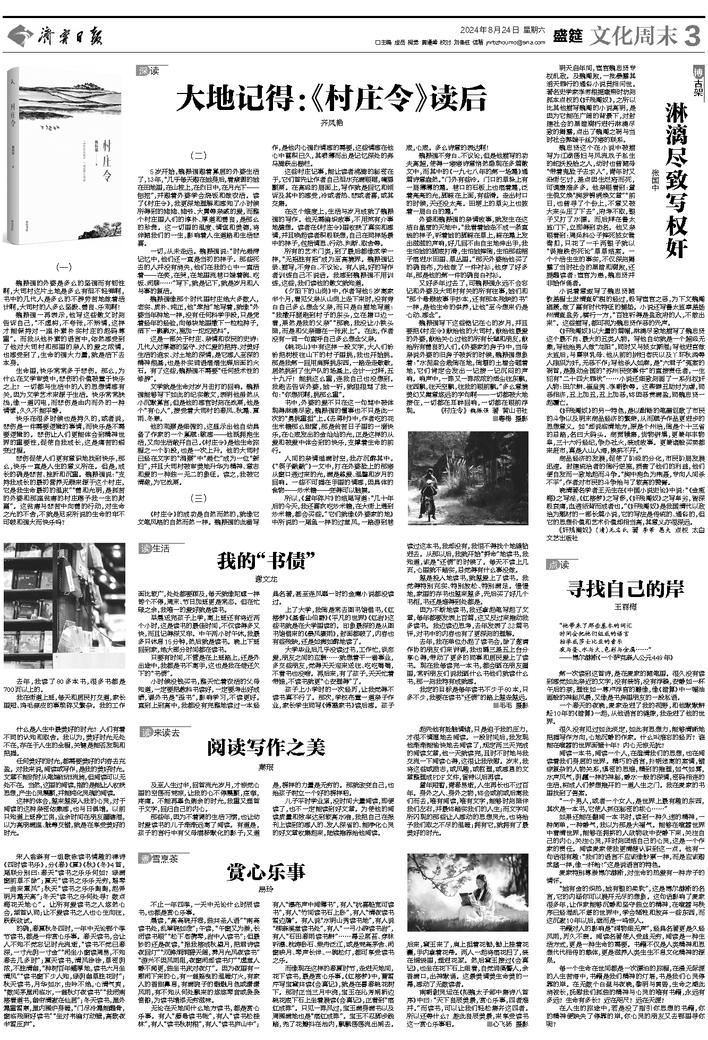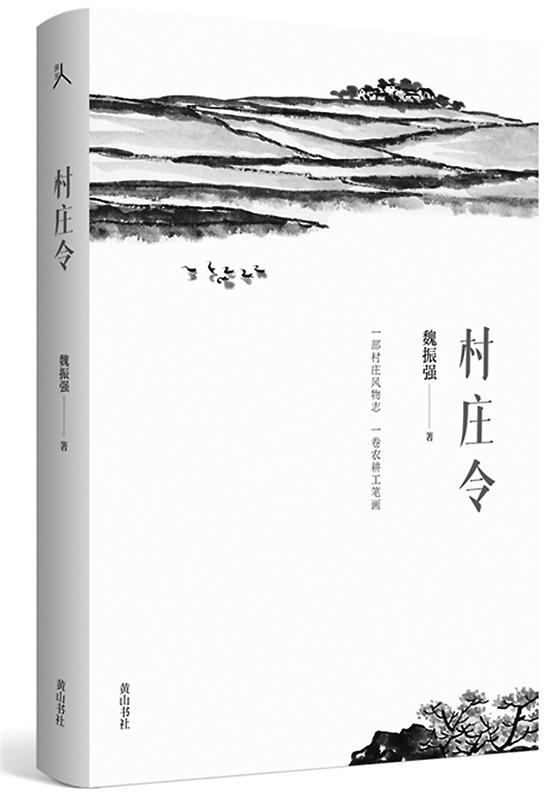(一)
魏振强的外婆是多么的坚强而有韧性啊,大司村这片土地是多么有泪不轻弹啊,书中的几代人是多么的不辞劳苦地做着活计啊,大司村的人多么坚毅、善良、乐观啊!
魏振强一再表示,他写这些散文时刻告诉自己,“不虚构,不夸张,不矫情,这样才能保持对一座朴素朴实村庄的起码尊重”。而我从他朴素的语言中,依然感受到了他对大司村和那里的亲人的爱之浓情,也感受到了,生命的强大力量,就是活下去本身。
生命里,快乐常常多于悲伤。那么,为什么在文学审美中,悲伤的价值被置于快乐之上?一切都与生活中的人的思想情感有关,因为文学艺术来源于生活。快乐常常肤浅,像一道闪电,而悲伤是由内而外的一种情愫,久久不能平静。
快乐在很多时候也是持久的,或者说,悲伤是一件需要逻辑的事情,而快乐是不需要逻辑的。悲伤让人们更能体会到精神世界的重要性,促使自我成长,这是痛苦的蜕变过程。
悲伤促使人们更有意识地找到快乐,那么,快乐一直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但是,成长的确是悲苦、挫折和沉重。魏振强说:“支持我成长的最初营养无疑来源于这个村庄,它是我生命最初的温床”“善和光明,是孤苦的外婆和那座贫瘠的村庄赐予我一生的财富”。这贫瘠与悲苦中向善的行动,对生命之光的不舍,不就是尼采所说的生命的牢不可破和强大而快乐吗?
(二)
5岁开始,魏振强跟着寡居的外婆生活了,13年,“几乎每天跟在她身后,看瘦弱的她在田地里,在山坡上,在烈日中,在月光下——刨挖”,并跟着外婆学会烧饭和做农活。读了《村庄令》,我更深地理解和感知了小时候所得到的姥姥、姥爷、大舅等亲戚的爱,而整个村庄里人们的淳朴、厚道和善良,是那么的珍贵。这一切里的温度、情谊和美德,将伴随我们的一生,影响着人生道路和生活悲喜。
一切,从未走远。魏振强说:“时光凝滞记忆中,他们还一直是当初的样子。那些死去的人并没有消失,他们在我的心中一直活着——在笑,在哭,在地里流巷口端着碗、吃饭、闲聊……”写下,就是记下,就是岁月和人与事的复活。
魏振强像那个时代里村庄绝大多数人,老实、质朴、纯正,他“笨拙”地写着,就像“外婆当年种地一样,没有任何科学手段,只是凭着经年的经验,向每块地里撒下一粒粒种子,洒下一瓢瓢水,施加一坨坨肥料”。
这是一部关于村庄、亲情和农民的史诗:几代人对厚德的坚守、对仁爱的把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土地的深情,是它感人至深的精神根基,也是朴实词语熠熠生辉后面的火石。有了这些,魏振强不需要“任何技术性的修辞”。
文学就是生命对岁月击打的回响。魏振强能够写下如此的纪实散文,表明他虽然从小沉默寡言,但是他的感官时刻在战栗,他是个“有心人”,接受着大司村的春风、秋霜、夏雨、冬寒。
他的观察是细微的,这显示出他自幼具备了作家的一个禀赋:敏感——他既拥抱生活,又向生活敞开自己。《村庄令》是他生命旅程之一个阶段,也是一次上升。他的大司村已经在文字的“洞察”中“凝伫”成为一位“新妇”,并且大司村被审美地升华为精神、意志和爱的一种独一无二的象征。读之,我被它清澈,为它战栗。
(三)
《村庄令》的成功是自然而然的,就像它文笔风格的自然而然一样。魏振强的此番写作,是他内心强烈情感的需要,这些情感在他心中蓄积已久,其喷薄而出是记忆深处的奔马腾跃出栅栏。
这些村庄记事,能让读者沸腾的秘密在于,它们首先让作者自己泪水充满眼眶,嘴唇颤栗。在高级的层面上,写作就是回忆和倾诉及其中的感受,冷或者热、悲或者喜,或其交集。
在这个维度上,生活与岁月成就了魏振强的写作。他无需编织故事,不用煞有介事地臆想。读者在《村庄令》里收获了真实和感情,并且唤起读者积极联想,自己在同样场景中的样子,包括情思、行动、判断、取舍等。
所有的艺术门类,到了最后都像武学一样,“无招胜有招”成为至高境界。魏振强记录、描写,不旁白、不议论。有人说,好的写作者训练自己不说话。我感到魏振强不用训练,这些,我们读他的散文就知道。
《夕阳下的山岗》中,作者写他5岁离家半个月,看见父亲从山岗上走下来时,没有旁白自己多么想念父亲,而只是白描地写道:“我撒开腿跑到村子的东头,立在塘口边一看,果然是我的父亲”“那晚,我没让小铁头陪,而是和父亲睡在一张床上”。在此,作者没有一词一句直呼自己多么想念父亲。
《桃花山》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大人们纷纷把树枝往山下的村子里挑,我也开始挑。那是我第一回用肩膀挑东西,一路走走歇歇,居然挑到了生产队的场基上,会计一过秤,五十九斤!能挑这么重,连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跑去告诉外婆,她一听,就狠狠骂了我一句:“你想死啊,挑那么重”。
书中,外婆的爱不只在这一句骂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魏振强的懂事也不只是此一次的“勇挑重担”上。《去蒋村》中,作者吃的花生米糖那么甜蜜,那是贫苦日子里的一滴快乐,在心底发出的金灿灿的光,正是这样的从爱和被爱中体会到的快乐,支撑着生命的前行。
人间的亲情溢满时空,我亦沉醉其中。《“筷子戳戳”》一文中,打在外婆脸上的那缕从窗口透过来的光,满是慈爱、温馨和岁月的回响。一些不可握在手里的情感,因具体的食物——炒米糖——变得可以触摸。
所以,《童年碎片》的结尾写道:“几十年后的今天,我还喜欢吃炒米糖,在大街上遇到炒米糖,都会买些。”它们就像《外婆家的地》中所说的一尾鱼一样的过堂风,一路游到巷底,心底。多么诗意的表达啊!
魏振强不旁白、不议论,但是他描写的功夫高超,使得一缕缕诗意悄然隐现在多篇散文中,而其中的《一九七八年的第一场霜》通篇诗意盎然。“门外有些冷。门口的草垛上有一层薄薄的霜。巷口的石板上也落着霜,泛着亮亮的光,脚踩在上面,有些滑。走出村口的时候,天还没太亮。田埂上的草尖上也披着一层白白的霜。”
外婆和魏振强的亲情故事,就发生在这洁白晶莹的天地中。“我看着她走不成一条直线的样子,听着她的脚踩在草上,踩在霜上发出滋滋的声响,好几回不由自主地伸出手,我生怕她的脚底打滑,生怕她摔倒,生怕那些稻子落进水田里、草丛里。”那天外婆给他买了的确良布,为他做了一件衬衫,他穿了好多年,那是他的第一件的确良白衬衫。
又好多年过去了,可魏振强永远不会忘记和外婆及大司村有关的所有往事,她们和“那个悬疑故事手抄本,还有那本残缺的书”一样,是他生命的供养,让他“至今想来仍是心动、感念”。
魏振强写下这些铭记在心的岁月,并且要把《村庄令》献给他的大司村,献给他最爱的外婆,献给关心过他的所有长辈和朋友,献给所有善良的人们。《外婆家的房子》中,当母亲说外婆的旧房子被拆的时候,魏振强想象着:“水泥梁会栽倒在地,倒塌的土墙会砸着地,它们肯定会发出一记接一记沉闷的声响。响声中,一阵又一阵浓浓的烟尘往东飘,往西飘,往天空飘,往我的眼前飘。”多么意境美幻又寓意悠远的字句啊——一切都被大地接住,一切都在耳畔回响,一切都在眼前浮现。《村庄令》 魏振强 著 黄山书社
■粤梅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