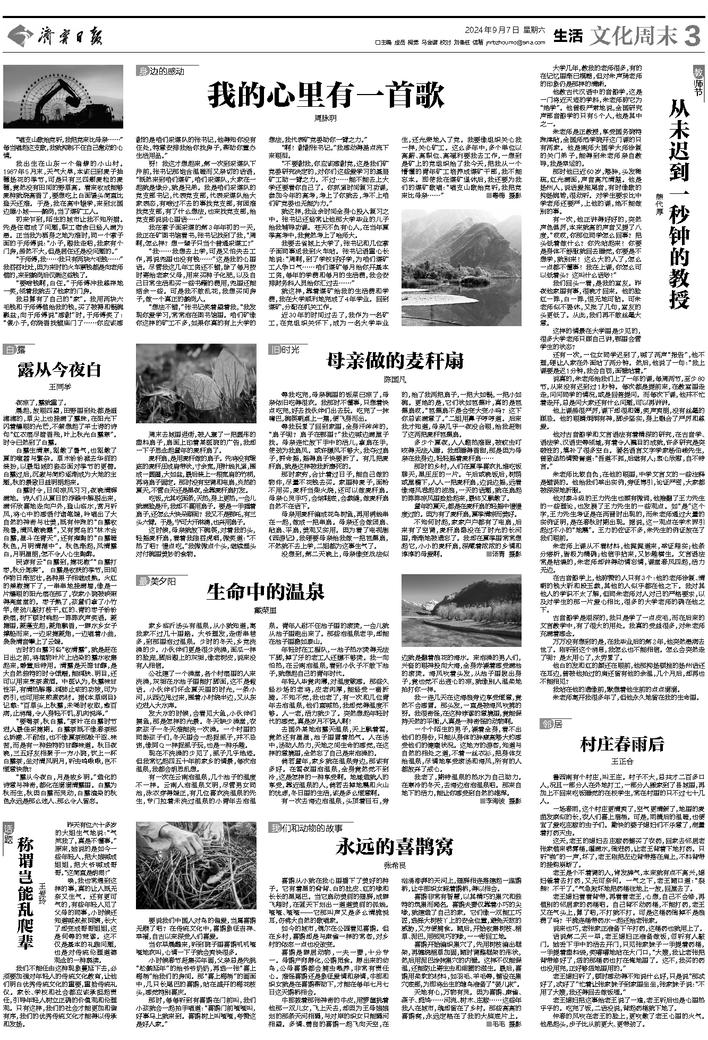大学几年,教我的老师很多,有的在记忆里渐已模糊,但对朱声琦老师的印象仍是那样的清晰。
他教古代汉语中的音韵学,这是一门将近灭迹的学科,朱老师称它为“绝学”。他曾极严肃地说,全国研究声部音韵学的只有5个人,他是其中之一。
朱老师是正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师范学院开这门课的只有两家。他是南师大国学大师徐复的关门弟子,能得到朱老师亲自教导,我是幸运的。
那时他已近60岁,矮胖,头发稀疏,红光满面,声音高亢清越。他是扬州人,说话爱拖尾音,有时像歌的抑扬婉转,很动听。对学生要求比中学老师还要严,上他的课,绝不能做别的事。
有一次,他正讲得好好的,突然声色俱厉,本来就高的声音又提了八度,“哎哎,你那位同学怎么回事?把头低着做什么?你先站起来!你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回去睡觉,你要是不想学,就别来!这么大的人了,怎么一点都不懂事!我在上课,你怎么可以低着头?这叫什么话唦!”
我们回头一看,是我的室友。昨夜他家里有事,很晚才回来。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恨无地可钻。可朱老师似不罢休,又批了几句,室友的头更低了。从此,我们再不敢丝毫大意。
这样的情景在大学里是少见的,很多大学老师只顾自己讲,哪里会管学生的状态?
还有一次,一位女同学迟到了,喊了两声“报告”,他不理,硬让人家在外面站了两分钟。然后,他说了一句:“我上课要是迟1分钟,我会自罚,面壁站着。”
说真的,朱老师给我们上了一年的课,每周两节,至少80节,从来没有迟到过1秒钟。每次都是提前来,在教室里走走,问问同学的情况,或是回答提问。而每次下课,他并不忙着走开,总是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讲。
他上课虽很严厉,课下却很和蔼,笑声爽朗,没有丝毫的顾忌。他的眼睛炯炯有神,脚步坚实,身上融合了严厉和慈爱。
他对古音韵学和文言语法有着精深的研究,在古音学、语法学、汉语史等领域,有着令人瞩目的成就,许多研究是突破性的,填补了很多空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杨伯峻先生,曾致函热情赞誉道:“吾道不孤,后继有人;衷心欣慰,自不待言。”
朱老师比较自负,在他的眼里,中学文言文的一些注释是错误的。他给我们举出实例,旁征博引,论证严密,大家都被深深地折服。
他对泰斗级的王力先生也颇有微词,他推翻了王力先生的一些理论,也发展了王力先生的一些观点。如“是”这个字,王力先生考证是在两晋时出现的,而朱老师通过大量的实例证明,是在春秋时期出现。据说,这一观点在学术界引起过不小的“地震”。王力的佐证不多,朱先生的例证放在了我们眼前。
朱老师上课从不看材料,他娓娓道来,举证翔实;他条分缕析,皆极为精确;他信手拈来,又妙趣横生。文言语法常是枯燥的,朱老师却讲得动情忘情,课堂春风四起,活力无边。
在古音韵学上,他称赞的人只有3个:他的老师徐复、清朝的钱大昕和段玉裁,其他的人似乎都在他之下。我对其他人的学识不太了解,但同朱老师对人对己的严格要求,以及对学生的那一片爱心相比,很多的大学老师的确在他之下。
古音韵学是艰深的,我只是学了一点皮毛,而在后来的文言教学中,有了很大的用处。我真的受益很多,对朱老师充满着感念。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我毕业后的第2年,他突然患病去世了。刚听到这个消息,我怎么也不能相信。怎么会突然走了呢?是太用心了,太劳累了。
他白的发和红的颜还在眼前,他那抑扬顿挫的扬州话还在耳边,曾被他拍过的肩还留有他的余温,几个月后,却再也不能相见?
我站在他的遗像前,默想着他生前的点点滴滴。
朱老师离开我很多年了,但他永久地留在我的生命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