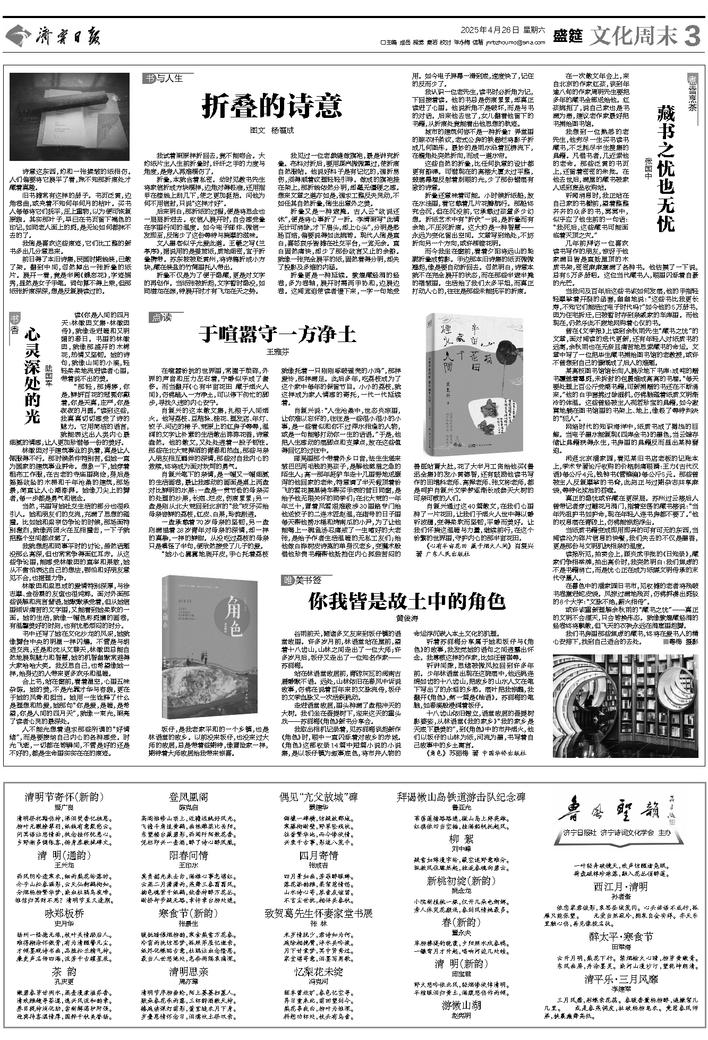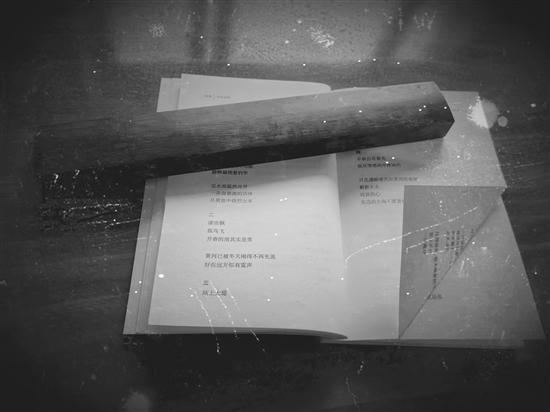诗意这东西,约和一张揉皱的纸相仿。人们偏要将它展平了看,殊不知那折痕处才藏着真趣。
旧书摊常有这样的册子。书页泛黄,边角卷曲,或夹着不知何年何月的枯叶。买书人每每将它们抚平,压上重物,以为便可恢复原貌。其实那叶子,早已在书页留下褐色的印记,如同老人面上的斑,是无论如何都抹不去的了。
我倒是喜欢这些痕迹,它们比工整的新书多出几分意思来。
前日得了本旧诗集,民国时期线装,已散了架。翻到中间,忽然掉出一张折叠的纸片。展开一看,竟是半阙《蝶恋花》,字迹娟秀,显然是女子手笔。词句算不得上乘,但那纸张折痕深深,想是反复展读过的。
我试着照原样折回去,竟不能吻合。大约纸片主人生前折叠时,纤纤之手的力度与角度,是旁人再难模仿了。
折叠,本就含着私密。幼时见教书先生将家信折成方块模样,边角对得极准,还用指甲在棱线上刮几下,使之更加挺括。问他为何不用信封,只说“这样才好”。
后来明白,那折纸的过程,便是将思念也一层层折进去。收信人展开时,自会感受叠在字里行间的温度。如今电子邮件、微信一发即至,反倒少了这份等待与揣摩的滋味。
文人墨客似乎尤爱此道。王羲之写《兰亭序》,据说用的是蚕茧纸,质地细密,宜于折叠携带。苏东坡被贬黄州,将诗稿折成小方块,藏在装盐的竹筒里托人带出。
折叠不仅是为了便于隐藏,更是对文字的再创作。当纸张被折起,文字暂时隐没,如同潜龙在渊,待展开时才有飞龙在天之势。
我见过一位老裁缝做旗袍,最是讲究折叠。布料对折后,要用蒸汽微微熏过,使折痕自然服帖。他说好料子是有记忆的,强折易伤,须得顺着纹理轻轻引导。做成的旗袍挂在架上,那折线依然分明,却毫无僵硬之感。想来文章之道亦如是,强求工整反失灵动,不如任其自然折叠,倒生出意外之美。
折叠又是一种遮掩。古人云“欲说还休”,便是将心事折了一折。李清照写“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分明是愁肠百结,偏要说得如此婉转。现代人倒是直白,喜怒哀乐皆摊在社交平台,一览无余。直白固然痛快,却少了那份欲言又止的余韵。就像一张完全展平的纸,固然看得分明,却失了投影及多维的内涵。
折叠更是一种延续。敦煌藏经洞的经卷,多为卷轴,展开时需两手协和,边展边卷。这阅览迫使读者慢下来,一字一句地受用。如今电子屏幕一滑到底,速度快了,记住的反而少了。
我认识一位老先生,读书时必折角为记,下回接着读。他的书总是伤痕累累,却真正读进了心里。他说折角不是破坏,而是与书的对话。后来他去世了,女儿翻看他留下的书籍,从折痕处竟能看出他思想的轨迹。
城市的建筑何尝不是一种折叠?弄堂里的晾衣杆条纹,老式公房的铁栅栏将影子折成几何图形。最妙的是雨水沿着瓦楞流下,在檐角处突然折向,而成一道水帘。
这些自然的折叠,比任何执意的设计都更有韵律。可惜现在的高楼大厦太过平整,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少了那份错落有致的诗意。
折叠还意味着可能。小时候折纸船,放在水洼里,看它载着几片花瓣航行。那船终究会沉,但在沉没前,它承载过孩童多少幻想。折纸艺术中有“折伏”一说,是折叠而有余地,不压死折痕。这大约是一种智慧——永远为变化留出空间。文章写到绝处,不妨折向另一个方向,或许柳暗花明。
而今我坐在窗前,看着夕阳将远山的轮廓折叠成剪影。手边那本旧诗集的纸页微微翘起,像是要自动折回去。忽然明白,诗意本就不在完全展开的状态,而在那些半遮半掩的褶皱里。生活给了我们太多平坦,而真正打动人心的,往往是那些未能抚平的折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