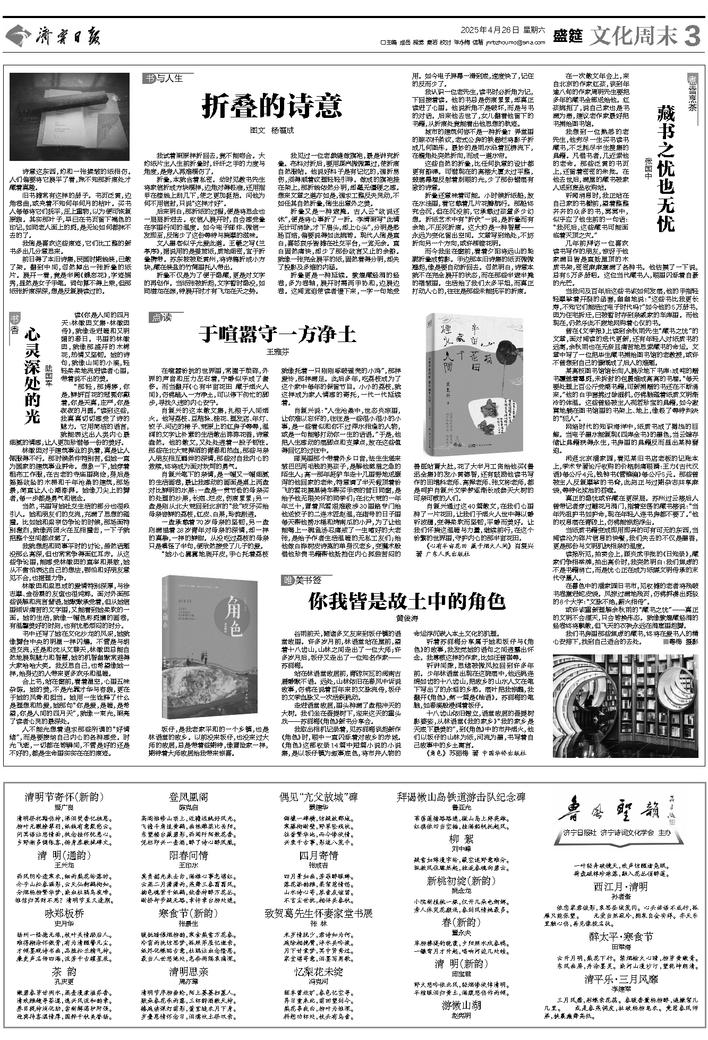在一次散文年会上,来自北京的作家红孩,谈到年逾八旬的作家周明先生要把多年的藏书全部送给他。红孩婉拒了,说自己家也是书满为患,建议老作家最好把书捐给图书馆。
我想到一位熟悉的老先生,他穷尽一生买书读书藏书,不乏耗尽半生搜集的典籍。凡借书者,几近索他的老命。那些泛黄的书页上,还留着密密的朱批。在他去世后,满屋的藏书被家人送到废品收购站。
听闻消息时,我正站在自己家的书橱前,望着整整齐齐的众多的书,冥冥中,似乎应了他生前的一句话:“我死后,这些藏书可能面临着灭顶之灾。”
几年前拜访一位喜欢读书写作的朋友,惊讶于他家满目皆是直抵屋顶的木质书架,密密麻麻塞满了各种书。他估摸了一下说,总有5万多册吧。这位当代藏书人,眼里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当我问及百年后这些书该如何发落,他的手指轻轻摩挲着开裂的函套,幽幽地说:“这些书比我更长寿,不知它们能活过电子时代吗?”如今他的5万册书,因为住宅拆迁,已被暂时存到亲戚家的车库里。而他现在,仍然乐此不疲地网购着心仪的书。
曾在《文学报》上读到余秋雨先生“藏书之忧”的文章,面对阅读的迭代更新,还有年轻人对纸质书的远离,余秋雨也在无奈且痛苦地思索藏书的命运。文章中写了一位把毕生藏书捐给图书馆的老教授,或许不曾想到自己的慷慨成了后人的难题。
某高校图书馆馆长向人展示地下书库:成吨的赠书覆盖着霉斑,未拆封的包裹堆成高高的书墙。“每天要处理上百公斤受潮书籍,可新捐赠的书还在不断涌来。”他的白手套拂过除湿机,仿佛触碰着纸质文明渐冷的体温。这些曾经被主人视若珍宝的典籍,如今寂寞地躺在图书馆里的书架上、地上,像极了等待判决的“犯人”。
网络时代的知识海洋中,纸质书成了搁浅的巨鲸。当电子墨水能复现《四库全书》的墨色,当云端存储让典籍获得永生,书房里的典籍反而显出某种窘迫。
闲逛北京潘家园,看见某旧书店老板的记账本上,学术专著论斤收购的价格刺痛眼睛:王力《古代汉语》每公斤4元,钱钟书《管锥编》每公斤5元。那些曾被主人反复摩挲的书脊,此刻正与过期杂志共享麻袋,等待化浆池的吞噬。
真正的隐忧或许藏在更深层。苏州过云楼后人曾带记者穿过雕花月洞门,指着空荡的藏书楼说:“当年先祖护书如护命,现在年轻人连书房都不要了。”他的叹息落在青砖上,仿佛能惊起浮尘。
当纸质书籍变成即用即弃的可有可无的东西,当阅读沦为碎片信息的快餐,我们失去的不仅是墨香,更是那份与文明肌肤相亲的温度。
读报所见,拍卖会上,顾炎武手批的《日知录》,藏家们争相举牌,拍出高价时,我突然明白:我们焦虑的不是书籍消亡,而是忧心正在成为纸媒文明传承的末代守墓人。
在暮色中的潘家园旧书市,见收摊的老者将残破书卷塞进蛇皮袋。风掠过满地残页,仿佛拼凑出斑驳的8个大字:“文脉不绝,薪火相传”。
或许该重新理解余秋雨的“藏书之忧”——真正的文明不会湮灭,只会转换形态。就像敦煌藏经洞的经卷终将飘散,但飞天的衣袂永远在洞窟里起舞。
我们书房里那些焦虑的藏书,终将在爱书人的精心安排下,找到自己适合的去处。■粤梅 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