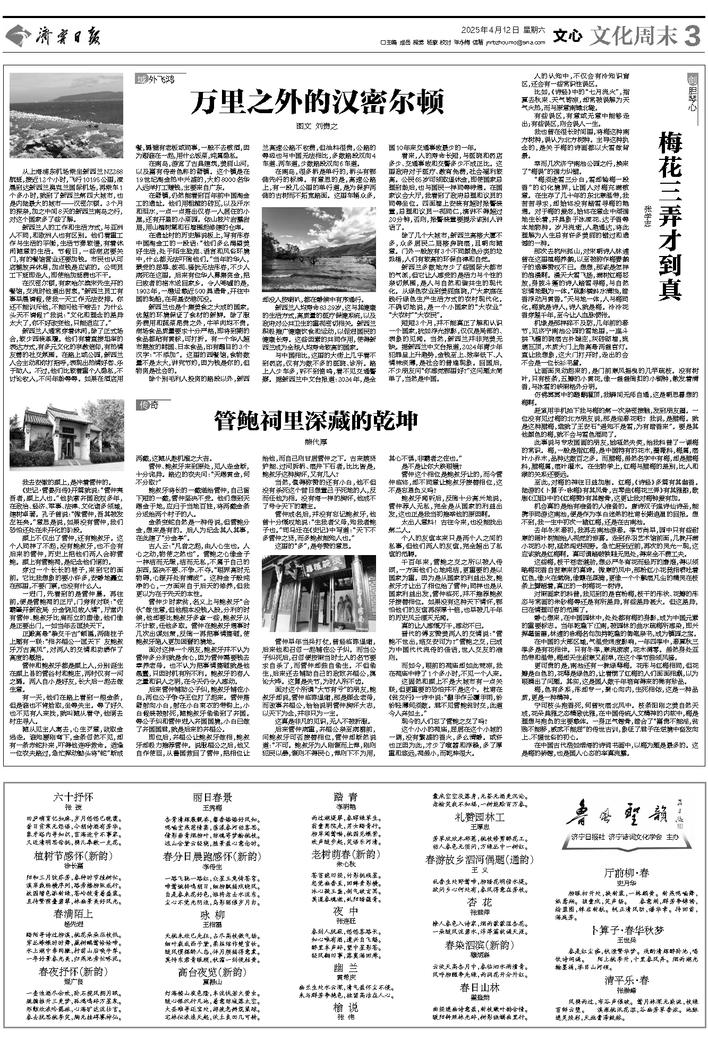人的认知中,不仅会有冷知识盲区,还会有一些常识性误区。
比如,《诗经》中的“七月流火”,指夏去秋来、天气转凉,却常被误解为天气火热,而与原意南辕北辙。
有些误区,有意或无意中能够走出;有些误区,则会误人一生。
我也曾在很长时间里,将梅这种南方树种,误认为北方树种。主导这种执念的,是关于梅的诗画都以大雪做背景。
幸而几次济宁南池公园之行,换来了“梅误”的强力纠错。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的幻化境界,让国人对梅充满敬意。在生存了几十年的东北寒温带,我苦苦寻求,却始终没有踏雪寻梅的艳遇。对于梅的爱恋,始终在意念中顽强地生长着,并具象于冰凌花、达子香等本地物种。岁月流逝,人趋通达,将此理解为人生总有许多美丽的错过和遗憾的一种。
那次去杭州孤山,对宋朝诗人林逋曾在这里植梅养鹤,以至被称作梅妻鹤子的逸事赞叹不已。想想,那该是怎样的浪漫啊。漫天大雪飞扬,满树红梅怒放,身披斗篷的诗人踏雪寻梅,与自然忘情地融为一体。“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天与地一体,人与梅同化,梅就是诗人,诗人就是梅。冷冷花香穿越千年,至今让人血脉偾张。
机缘是那样猝不及防,几年前的春节,见济宁南池公园的雪地里,一座斗拱飞檐的院落古朴端庄,灰砖砌墙,琉璃瓦顶,木质大门上角高悬两盏宫灯。直让我想象,这大门打开时,走出的会不会是一位长衫书童。
让画面灵动起来的,是门前寒风摇曳的几竿疏枝。没有树叶,只有枝条,五瓣的小黄花,像一盏盏倒扣的小铜钟,散发着清香,与冰雪的映照格外分明。
仿佛冥冥中的醍醐灌顶,我瞬间无师自通,这是朝思暮想的梅啊。
赶紧用手机拍下我与梅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发到朋友圈。一位没有见过梅的北方朋友说,那是迎春花吧?我说,是腊梅。就是这种腊梅,造就了王安石“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要是其他颜色的梅,就不会与雪色混同了。
此事说与专攻国画的朋友,她哑然失笑,给我科普了一课梅的常识。梅,一般是指红梅,是中国特有的花木,蔷薇科,梅属,落叶小乔木,品种达数百之多。而腊梅,虽然名字中有梅,却是腊梅科,腊梅属,落叶灌木。在生物学上,红梅与腊梅的差别,比人和猴的关系还要远。
至此,对梅的神往日益加剧。红梅,《诗经》多篇有其幽香。陆游的《卜算子·咏梅》有其风骨,古琴曲《梅花三弄》有其雅韵,歌剧《江姐》中的《红梅赞》有其傲骨,这更让我对梅钟爱有加。
机会真的是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的。唐诗双子座诗仙诗圣,能携手同游这南池,便是作为李白迷弟的杜甫长期追星的回报。想不到,我一生中初次一睹红梅,还是在古南池。
去年冬末春初,我再去南池游春。季节尚早,园中只有些耐寒的阔叶树能给人视觉的惊喜。走到乔羽艺术馆前面,几株开满小花的小树,猛然闯进视野。急忙赶到近前,再次的灵光一现,这应该就是红梅啊。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些梅,枝干苍老遒劲,想必严冬育花而经历的磨难,得以领略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真谛。微寒的风中,那粉红小花竞相喷吐着红色,像火在燃烧,像霞在蒸腾,更像一个个飘落凡尘的精灵在枝条上舞蹈着,真正的一树梅花一树诗。
对照画家的科普,我见到的是宫粉梅,枝干的形状、花瓣的形态与常画的朱砂梅等还是有所差异,有些差异甚大。但这差异,已在情理可容的范围了。
静心想来,在中国园林中,处处都有梅的身影,成为中国元素的重要标志。当年乾隆下江南,被园林的曲水疏梅所感染,即兴挥毫留墨,林逋的咏梅名句加持乾隆的御笔亲书,成为镇园之宝。
在中国的大部区域,气温受纬度影响,一年四季中,春夏秋三季多是有花相伴。只有冬季,寒流滚滚,花木凋零。虽然身处亚热带和温带,梅却天生耐寒又耐旱,在这个季节独领风骚。
更可贵的是,南池还有一株绿萼梅。花形与红梅相同,但花瓣是白色的,花萼是绿色的,让看惯了红梅的人们面面相觑,以为眼睛出了问题。其实,这是国人数千年培育得来的稀有珍品。
梅,色有多系,形却专一,聚心向内,生死相依,这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精神。
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枝条阳刚之美自然天成,花朵典雅之态精致优雅,在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内核中,梅是理想与抱负的主要载体。一身正气傲骨,暗合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世古训,象征了君子在逆境中奋发向上、不媚世俗的初心。
在中国古代浩如烟海的诗词书画中,以梅为题是最多的。这是梅的骄傲,也是国人心态的率真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