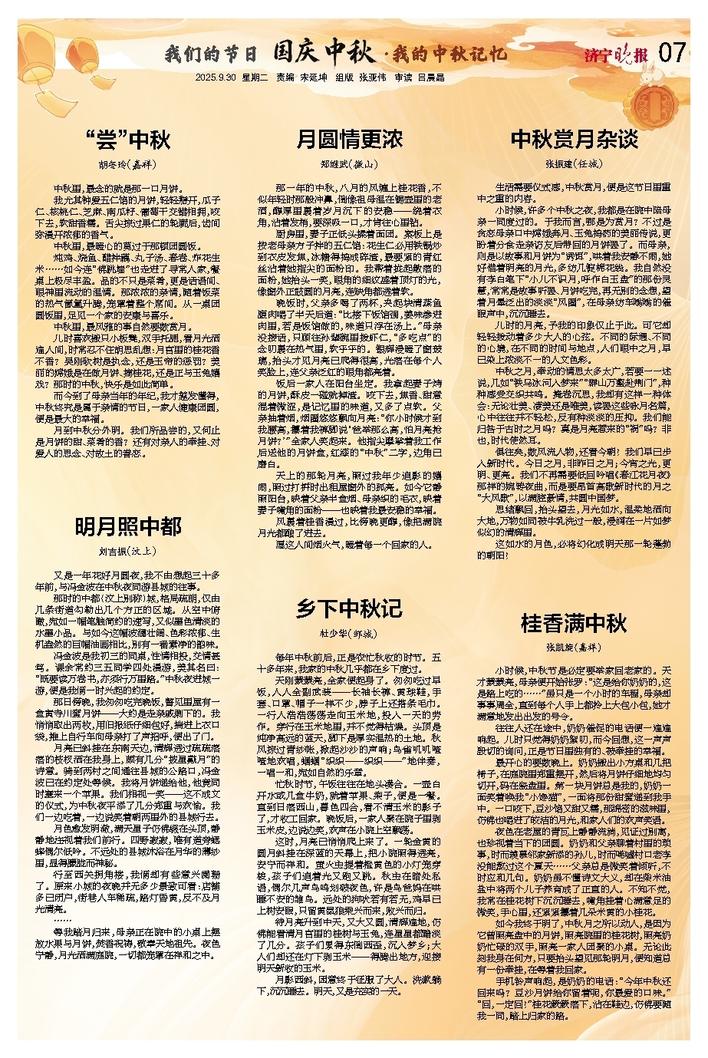杜少华(邹城)
每年中秋前后,正是农忙秋收的时节。五十多年来,我家的中秋几乎都在乡下度过。
天刚蒙蒙亮,全家便起身了。匆匆吃过早饭,人人全副武装——长袖长裤、黄球鞋,手套、口罩、帽子一样不少,脖子上还搭条毛巾。一行人浩浩荡荡走向玉米地,投入一天的劳作。穿行在玉米地里,并不觉得枯燥。头顶是纯净高远的蓝天,脚下是厚实温热的土地。秋风掠过青纱帐,掀起沙沙的声响;鸟雀叽叽喳喳地欢唱,蝈蝈“织织——织织——”地伴奏,一唱一和,宛如自然的乐章。
忙秋时节,午饭往往在地头凑合。一壶白开水或几盒牛奶,就着苹果、梨子,便是一餐。直到日落西山,暮色四合,看不清玉米的影子了,才收工回家。晚饭后,一家人聚在院子里剥玉米皮,边说边笑,欢声在小院上空飘荡。
这时,月亮已悄悄爬上来了。一轮金黄的圆月斜挂在深蓝的天幕上,把小院照得透亮,安宁而祥和。萤火虫提着橙黄色的小灯笼穿梭,孩子们追着光又跑又跳。秋虫在暗处私语,偶尔几声鸟鸣划破夜色,许是鸟爸妈在哄睡不安的雏鸟。远处的狗吠若有若无,鸡早已上树安眠,只留黄鼠狼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待月亮升到中天,又大又圆,清辉遍地,仿佛能看清月宫里的桂树与玉兔,连星星都黯淡了几分。孩子们累得东倒西歪,沉入梦乡;大人们却还在灯下剥玉米——得腾出地方,迎接明天新收的玉米。
月影西斜,困意终于征服了大人。洗漱躺下,沉沉睡去。明天,又是充实的一天。